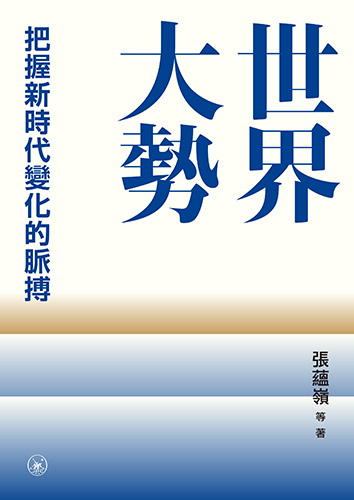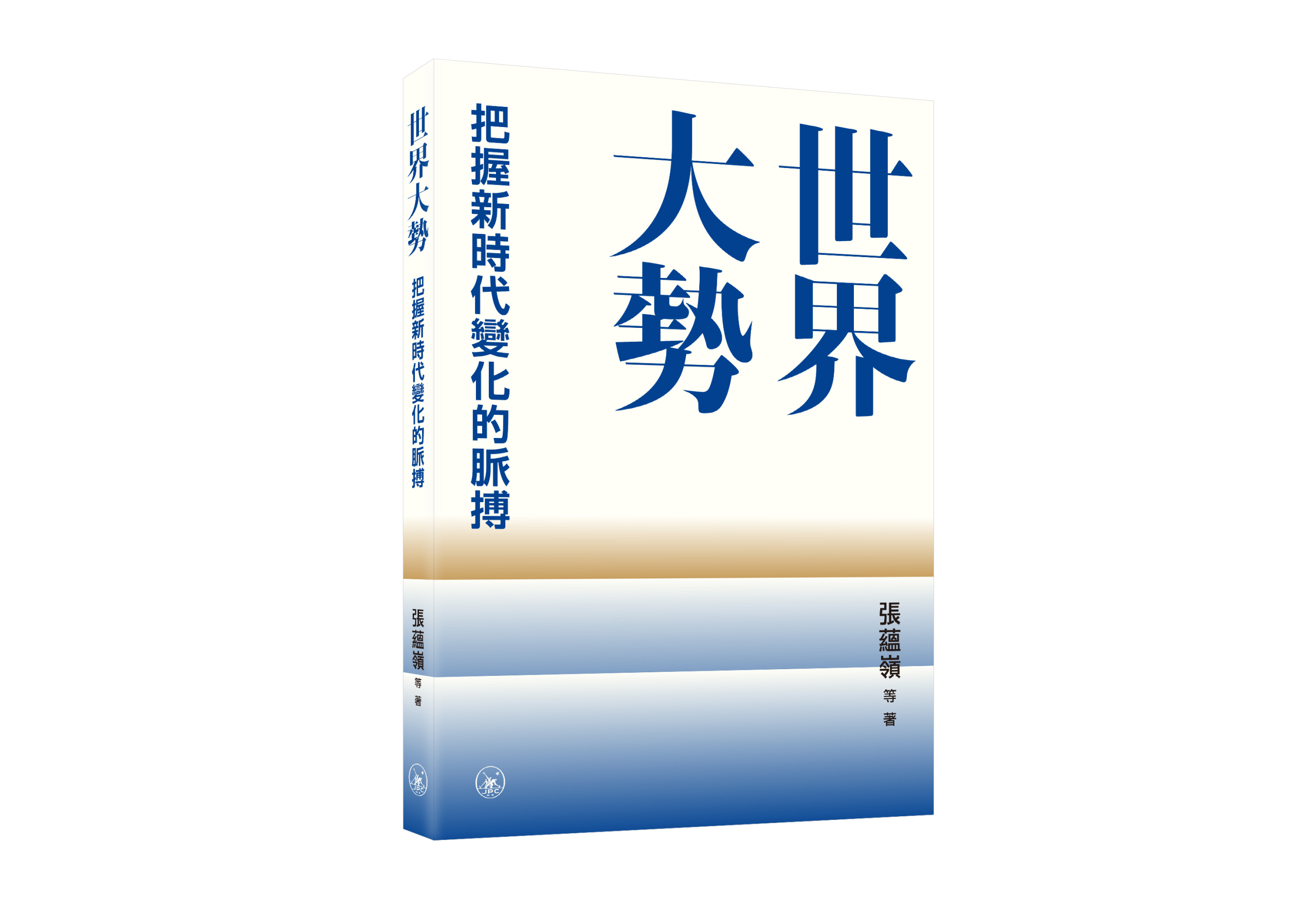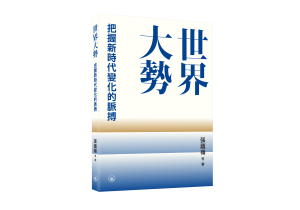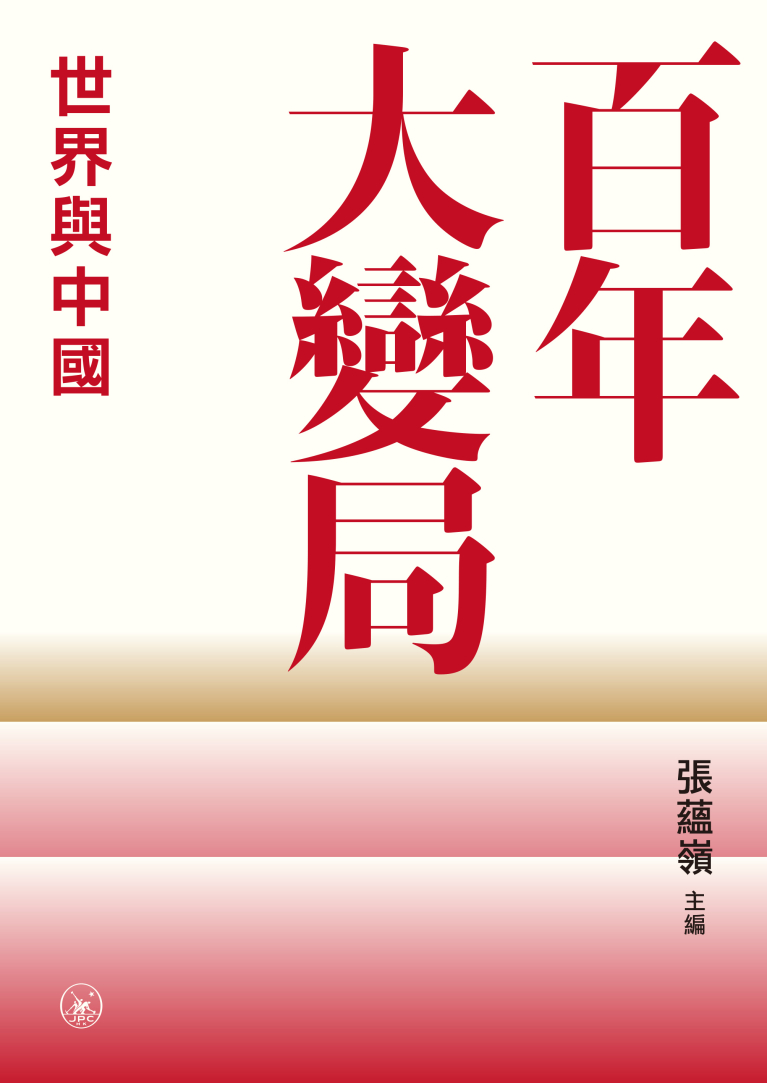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
簡介
前瞻未來發展大勢 解析中國發展之策
《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姊妹篇,旨在對大變局進一步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思考與謀劃,多角度對未來發展大勢進行前瞻性、戰略性、儲備性研究,回答了百年大變局下中國當如何把握未來發展大勢、應對挑戰、抓住機遇、實現發展、贏得未來。
本書特點:
★解答時代之問,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向何處去
★洞察世界,了解未來,把握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大勢
★立足新發展階段,解析中國發展之策
★內容豐富,語言通讀易懂
目錄
序言 i
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 朱鋒 001
一、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含義 001
二、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戰略大格局 003
三、中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008
四、國內政治進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 011
五、面向未來的大戰略思考 014
全球化調整與戰略機遇 / 張蘊嶺 022
一、反全球化浪潮 022
二、解析全球化 024
三、全球化是把“雙刃劍” 027
四、全球化進入調整期 030
五、新全球化不可阻擋 033
六、世界需要新共識 037
七、全球化與中國 039
八、面向未來的大戰略 043
世界經濟大變局與中國的大戰略 / 陳文玲 044
一、世界經濟形態和經濟格局的顛覆性變革 044
二、百年大變局與中國大戰略 060
中美關係:關鍵是掌控大局 / 賈慶國 076
一、衝突與合作的中美關係 076
二、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趨勢 090
三、總結:管控衝突,推動合作 100
全球治理:歷史、邏輯與中國角色 / 張宇燕 102
一、歷史回顧 103
二、問題與邏輯 107
三、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是大勢所趨 112
四、聚焦全球經濟治理 116
五、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路徑 119
基於新時代的“一帶一路”謀劃與建設 / 黃仁偉 張曉通 124
一、“一帶一路”的重大意義 124
二、“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與挑戰 130
三、面向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 137
大格局:“東亞奇跡”再造 / 江瑞平 144
一、世界百年大變局中的東亞 146
二、“東亞奇跡”再造中的中國 150
三、合作推進“東亞奇跡”再造 160
軍事與安全大戰略 / 唐永勝 169
一、國際安全治理的挑戰與機遇 170
二、國家安全需要創新軍事戰略思維 176
三、新軍事革命與軍事戰略 181
四、走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 186
周邊地區未來發展大勢 / 鍾飛騰 192
一、中國經濟崛起大勢 192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發展情結 196
三、處在歷史性轉變的東北亞 202
四、作為中國周邊外交優先方向的東南亞 205
五、跨越“龍象之爭”的陷阱 212
六、“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中亞 216
新海洋觀與海洋強國建設 / 張景全 219
一、新時代的海洋大戰略 220
二、海洋觀的歷史演變 226
三、新時代海洋觀 231
四、面向未來的海洋戰略謀劃 238
面向未來的中國大戰略 / 門洪華 244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衝擊 245
二、外部環境的演變 248
三、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 252
四、創新發展的戰略設計 255
五、面向未來的大戰略 257
作者簡介
張蘊嶺
男,1945年5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安全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國內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曾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是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東亞展望小組成員,中國—東盟合作官方專家組成員,亞歐合作專家組亞洲代表成員,東亞自由貿易區可行性研究專家組組長,東亞經濟夥伴關係可行性研究專家組成員,中韓聯合專家委員會中方主席,中韓友好協會副會長,德意志銀行亞太地區顧問等。
主要代表專著有:《世界經濟中的相互依賴關係》、《未來10—15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中國與亞洲區域主義》(英文)《世界市場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與世界:新變化、新認識與新定位》《構建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尋求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等。
序言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主編的上一本書,即《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該書主要從總體框架和重要領域分析了大變局的內涵、內容與特徵。本書定名為《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旨在對大變局進一步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思考與謀劃。變局既有挑戰,也有機遇,因此,基於大戰略謀劃未來,既包括如何應對挑戰,也包括如何抓住機遇,無論是應對挑戰,還是抓住機遇,都需要創新。既然是進行大戰略思考與謀劃,就需要有大視野、大思路、大胸懷,既立足中國,又放眼世界。
不確定性是大變局的一個突出特徵,一是沒有現成的答案可用,二是任何答案都需要經過艱辛的試驗。儘管如此,對於發展的大勢還是可以研判的。以往的大變局獲得答案總是要經歷大戰,在新時代,也許可以走出這種看似必然的陷阱,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在未來,世界的相互依賴與一體性特徵會更強,而不是更弱。儘管當今反全球化的勢力上位,但擋不住國家開放、世界開放的洪流。氣候變化把人類“逼上梁山”,使得世界向新發展範式的轉變不可逆轉。變局之下必然有亂,但新格局也在孕育之中,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競爭,也要合作,是各國多數人民的共識,因此,把大局把握好,世界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一、應對變的挑戰
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大變局,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都是如此。大變局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多個層面,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情況,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問題,即全球性問題。作為大戰略思考,我們聚焦那些具有重大、重要影響的大變化、大趨勢。
在經濟層面,嚴峻的挑戰是發展範式需要改變,多邊體系面臨危機,逆全球化趨勢上升,因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陷入困難期,在許多國家甚至陷入停滯。疫情期間,各國都採取了放量貨幣支持增長的政策,但難以長久。因此,短期而言,回歸正常發展,積聚新發展能量需要較長的時間。經濟是基礎,經濟環境向差的方向變化,會引發很多相關的問題。
在政治層面,嚴峻的挑戰是政治協同性變差,分裂加劇,國家內部、地區和世界都有這種趨勢。在不少國家,“政治保守主義”得勢,其主要的表現是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得到政治人士、集團勢力的支持,一些政治極端人物得勢,成為排外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的推手。值得重視的是,政治保守主義會加劇國內社會的矛盾,也可能會成為激發恐怖主義上升的重要因素,使得社會變得更不安寧。
在社會層面,嚴峻的挑戰是基於多種原因的社會分化加劇,既有排外主義引起的社會衝突,也有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對立。以往,社會的分裂主要發生在欠發達國家,而今,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的分裂表現得越突出。社會的分裂也必然反映為政治的分裂,從而使得社會政治的包容性降低,未來社會的不穩定性可能會加劇。
在國際關係層面,最為凸顯的是世界力量格局對比發生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力量格局決定着國際秩序關係與秩序的導向,世界力量格局轉變必然反映在格局與秩序重構的導向上。作為居於霸權地位的美國,一方面力爭承擔較少責任,另一方面又奮力保位,打壓競爭者,導致基本國際關係原則和秩序發生混亂,增加發生大對抗的風險。
新技術革命帶來很多新的挑戰,以智能技術為核心的技術變化的重要影響是改變現有經濟與社會運行的方式,引起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變革。在國際層面,改變技術和發展的競爭結構,具有綜合實力與能力的國家、企業集團領銜技術優勢,從而導致技術差距拉大,技術壟斷或者技術封堵將可能會阻斷技術擴散的路徑,使後進國家難以提升技術能力。由於技術鴻溝加大,一些後進國家可能被技術邊緣化。
氣候變化加速,最嚴峻的挑戰是改變地球生態環境,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嚴重威脅。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特別是工業化以來溫室氣體排放與生態環境破壞直接相關。阻止氣候變暖需要各國集體行動,承擔責任,加快傳統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變革,而國際利益之爭、變革與發展的矛盾等阻礙責任共識的形成與決斷行動的採取。與其他變化不同,氣候變化涉及全局、全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變勢已經不可阻擋,但需要阻止災難發生。
總的來看,世界進入一個“不確定期”,諸多挑戰前所未有,悲觀者甚至認為,世界會陷入一種“無序”的動盪狀態。因此,積極應對挑戰,以戰略高度謀劃,防止局勢向更壞的方向發展,特別是要阻止發生大的戰爭,這是大變局時期應對挑戰最需要做的。
二、抓住變的機遇
世間沒有不變的事物,變是常態,變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在多數情況下,機遇只是一種潛在可能性,把可能性變為可行性,大多需要作出艱苦的努力。
在經濟領域,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經濟增長處於下行期,機遇在哪裏?分析經濟波動變化,可以基於兩個視角觀察:一是短週期波動,主要受到短期變化因素的影響,當前的經濟下行趨勢有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如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影響中斷了很多經濟活動,使得正常的經濟運行所需的供給鏈斷裂,增長進程中斷。同時,也受到美國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實施貿易制裁、全面戰略競爭等因素和突發的政治社會變動的影響。按照經濟週期運行的規律,在經過下降之後,經濟會復甦,通過調整重聚增長活力。二是長週期波動,一般為30年左右,主要受到大宗產品價格波動、技術革命、經濟結構變化以及新興經濟群體崛起等因素的影響。有的認為,傳統的短經濟週期規律已經不太明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從長週期的視角來觀察。目前,世界經濟正處在長週期的底部,經過一個時期的調整,將會進入上行狀態,而上行是經濟之變的機遇期。
其實,認識經濟之變帶來的機遇,不能僅從週期視角來分析,還應主要分析導致變化的大事態、大因素。在諸多因素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是當前已經進入實用階段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新的技術革命提供的機遇主要是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創新,生成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生產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範式轉向新範式,以智能技術為引領的技術創新也許會成為解決傳統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態惡化、氣候變化的一把鑰匙。還有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擴容與繼續群體發展等,將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因此,抓住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才能有更好的未來。
過去一個時期,發展中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儘管受到總體環境的影響,發展放慢,但新興經濟體有望擴大,如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都是人口大國,都具有巨大的後發發展優勢與巨大的增長潛力和能動力。
就國際關係與秩序格局變化來看,儘管存在發生對抗、衝突,甚至是戰爭的危險,但是,任何的轉變都孕育着向新關係格局與秩序轉化的機遇。權勢轉移是國際關係與秩序轉變的核心。所謂權勢(對應的常用英文是power),傳統上,就世界格局而言,主要是指一國對世界具有主導性或霸權地位的實力和能力。因而,權勢轉移主要是指由一國轉向另一國。
回顧一下歷史,真正能稱得上世界霸權的國家很少。歷史上權勢擴展到世界並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只有大英帝國,其權勢曾擴及世界,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權勢的衰落經歷了比較長的時間,被認為是自己從帝國的神壇上跌落下來的,進行了“和平的權勢轉移”。所稱“和平轉移”,主要是指英國的權勢由美國接替,英美之間並沒有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大戰。
按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具備了這樣的實力。美國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權勢推動了戰後國際體系的建立,但美蘇爭霸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國的權勢、能力。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後,美國才真正成為世界霸權國家。不過,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體系成為冷戰後佔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和規則,因而,人們往往把美國對世界的主導性權勢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如今,美國的權勢衰落,出現了權勢轉移的問題。在幾乎所有有關權勢轉移的話題中,都盯住了中美兩國。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霸權國家,特別是冷戰之後一家獨霸,而中國被認為是在美國之後綜合實力最強、最有潛力成為對世界擁有主導性權勢的國家。因此,中美對決似乎就成了權勢轉移的主戰場,成為影響世界格局和秩序走向的主線。
然而,時代不同了,實際的發展也許並非如此。新時代權勢轉移具有新的含義和方式。從世界發展的未來大趨勢看,由一個大國主導世界的時代難以再現。權勢轉移的新含義並不是由一個大國再傳給另一個大國,權勢會分化和分解,這種趨勢可以體現在多個層次:基於國家的權勢分化,走向多層次,一是更多國家參與,這種參與有些是通過自身的能力,有些則是通過制度性的參與;二是非國家實體權勢提升,這裏的非國家實體主要是指國際與區域組織、大公司集團以及有影響力的社團。同時,傳統權勢的體現主要是國家硬實力和與之相應的軟實力,在權勢分化與分解的情況下,國家也許不能再集權勢於一身。
就美國而言,其實,美國所體現的不主要是自身的衰落,而是權勢主導地位和控制力的衰落。一則美國付不起維持霸權的代價,同時也沒有能力再號令天下;二則世界變了,新趨勢是多樣性、多中心,美國面臨的是群體崛起的競爭。“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可行性,可能不是重塑霸權,而是重整分裂的社會和解決累積的自身問題。現實地看,被認為是挑戰者的中國所擁有的權勢肯定增大,但中國沒有替代美國做霸主的打算,中國承擔不了這個代價,也沒有能力做到,他者也許不會接受。
新時代,權勢轉移不等同於權勢替代,而是結構的改變,權勢由過度集中向分散化轉移。在此情況下,如果美國所關注的主要是由其領導創建的規則和體系不被顛覆,那麼與競爭者就有更多的共同話語權,因為捍衛體系的穩定、遵守基本規則也是後者同意的,並且是符合其基本利益的,後者所要求的主要是調整與改革,能夠反映其基本利益,這樣的調整,一是必要,二是對大家可能都有利。這可能就是國際格局變化、權勢轉移所能利用的機遇。
總之,在變化轉變期,存在向好發展的機遇。因此,抓住機遇,通過創新實現大局穩定與世界和平是可行的。
三、大戰略思考
(一)新發展觀
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在經歷歷史性轉變,需要判斷轉變的大趨勢,把握轉變的大機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主要得益於越來越開放與一體化的大市場。世界市場的開放主要基於多邊機制(GATT/WTO)的構建與推動,得到了各個國家實施的開放發展政策的支持,同時也得到了區域開放安排(FTA)的支持。開放的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使得各國特別是後起發展中國家有了可以進入世界市場、利用外部資源加快發展的環境,使得企業可以進行基於開放的區域和世界市場經營佈局,從而推動了企業全球化供應鏈的構建。
如今,環境發生變化,國家如何對未來進行發展戰略定位與政策導向?企業如何制定面向未來的經營戰略?這裏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要點需要考慮。
第一,世界由“自由放任的開放”向“平衡與有管理的開放”轉變,前者以實現市場最高水平的開放為目標,後者以實現經濟社會均衡為目標。這種轉變是對“自由放任的開放”所帶來的問題的糾正,而不是完全否定。新的開放也會適應和反映新的發展,特別是新技術經濟的發展,如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未來,世界市場的總體趨勢是在維護現有開放基本規則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適應新的技術經濟發展,體現新發展中經濟的需求,深化市場開放的內涵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均衡。就國家、企業而言,選擇開放、利用開放的世界市場發展是大戰略定位與實踐。
第二,由於傳統工業化發展範式所導致的綜合影響,世界經濟向新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和動力都在加強。新發展方式必然與新生活方式的發展相配合,形成可持續、均衡、包容的新發展結構。向新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主要來自不可持續的現實。以往,世界經濟發展基本上以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構建的傳統工業化發展範式為導向,先工業化的國家進入後工業化,把過時的產業轉向後起發展中國家,一波一波地傳遞,這樣導致越來越大的傳統工業化規模,越來越嚴重的排放和生態災難。轉變發展方式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這種轉變得益於人的新認知,即可持續的新發展觀,也得益於新技術的推動,即以節能環保的智能化技術為導向。因此,以新發展觀為指導,以新技術為推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
第三,在新發展方式的轉變中,經濟與社會的均衡會得到更多的重視。傳統發展方式優先重視資本導向下的增長,其結果導致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失衡,使得財富的積累更向資本集中;導致財富擁有的兩極化,使得中間階層萎縮,低收入人群增加。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產生了對市場的糾正,增加了政府參與經濟運行的功能,構建了社會保障體系。在新的發展方式中,需要進一步增加社會功能的因素,加強資本的社會功能導向與社會共享的構建。如關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就體現了資本對社會責任的要求,但僅僅這還不夠,需要更多的綜合社會政策設計和行動。比如,面對生產的智能化、無人化,歐洲一些國家開始進行“普遍性收入分配”試驗,研究在人與直接生產過程分離之後如何進行收入分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戰略思維和行動。
(二)全球治理
世界是一個整體,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高,涉及全球問題,沒有哪一個國家或者哪幾個國家能夠有能力解決。因此,需要加強國際治理制度建設,推動合作共進。
國際治理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大體可分為五類:其一,聯合國體系,從安理會的大國治理,到聯合國大會的集體性推動治理,還有為數眾多涉及各個領域的專門組織、區域委員會等。鑒於幾乎所有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因此,它們是具有代表性、普世性的國際體系。其二,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G)、地區性開發銀行等。迄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被納入這些組織框架,其制定的規則成為公認的國際規則和行為規範。其三,國際條約,涉及領域很多,如核不擴散條約、極地條約、氣候變化條約、海洋法等。作為國際條約、法律,它們具有超國家性,各締約國都有遵守的義務和職責。其四,行業規約。儘管它們不是政府間組織,不是政府簽署,但對於行業具有國際法規的作用,因為基於市場運行的規則,如果不遵守行規就不能開展業務,會受到處罰。如《巴塞爾協議》就是銀行間簽訂的規約。還有各種行業組織制定的不同規約,都是相關方必須遵守的。其五,國際對話合作機制。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七國集團(G7),作為發達國家的集合,它們通過對話、協商與合作,對世界經濟發揮導向的作用。2008年以後,二十國集團(G20)成立,集合了世界最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商世界經濟的發展大事,提出指導性共識文件。
國際治理具有普遍性特徵,無論在治理範圍還是在治理方式上,都在不斷發展。這種大趨勢與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國際經濟以及社會生活國際化發展相適應,沒有一個國家是處在獨立的自我空間而不受國際治理約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通過不斷發展的國際治理,世界進入了一個“有治理的國際秩序”,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成就。
基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聯合國,逐步把幾乎所有國家都納入一個體系之內,並且制定了具有普世價值的聯合國憲章和一系列公約,從而奠定了現代國家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的基本原則基礎。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性,聯合國並沒有走出大國治理的思維,比如,安理會給了一個大國至上的否決權,儘管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權勢的制衡,防止走偏,但這為大國利用特權和霸權提供了法權依據。再有,作為國際成員,退出國際條約、公約的成本太低,本來,在相互依賴的國際環境中,各國都有義務履行國際規約的責任,為此,應該把“退群”的門檻大大抬高,如果一國決意“退群”,也應該給予嚴格限制,甚至進行懲罰。比如,氣候變化關乎人類的共同生存,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的公約是各國應盡的義務,從法理的角度,應該是不能退出的,對於任何國家的退出,都理應根據其排放量制定相應的賠償標準。比如,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明確了共同遵守的責任,特朗普政府自行退出,這是失德、失責的,退出世衛組織(WHO)也是毫無道理的,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巴黎協定》,回歸世衛組織,是理所當然的。
世界需要新秩序,但就像任何一個歷史大勢的轉變一樣,這需要時間,也需要把握。如今和今後,涉及全球共性利益的問題越來越多,對全球治理的要求越來越高,其中,氣候變化排在首位。氣候變暖加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類生存和地球生態可持續的威脅日益嚴重。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也許是推進國際合作,加速發展方式與生活方式轉變,催生新技術,特別是新能源技術發展的驅動力。共同的危機驅動,使得各國沒有替代的選擇,只能直面,只能採取行動,必須依靠國際治理制度構建和國際社會集體參與才能有效應對挑戰和危機。這是新時代國際秩序構建的中心議題。
(三)維護和平
在大變局時期,防止大國衝突,特別是戰爭,是加強國際治理的首要任務。大國不同於中小國家,可動用的資源和人才多,可以成為先進技術、強大軍事的領先者,因此,憑藉實力擴張與稱雄的慾望往往很強。因此,從歷史上看,大戰爭實際上都是大國之戰。但是,現在和未來,大國之間發生大戰的代價越來越大,因此,發生大戰概率也可能會越來越小,因為任何一方都承受不了相互毀滅的代價,但也不可掉以輕心。
如今,我們看到,戰爭大都是發生在小國之間,或者國內對抗勢力之間,儘管背後往往都有大國介入的影子,但與歷史上不同的是,大國之間儘可能避開直接的衝突。按照上述新型權勢轉移的邏輯,即權勢轉移的典型特徵不是權勢替代,而是權勢的分解和分散,那麼,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權勢的有序與和平的轉移。按照這樣的邏輯,國際社會,包括守成大國和被認定為挑戰者的大國,就可以尋求共同的話語、協和的利益,容許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參與,讓競爭與合作並行,而不是僅僅聚焦在兩個大國你死我活的對抗上。
為此,在理論上、輿論上要建立新的話語體系,推動國際共識。事實上,各方角色參與新格局、新秩序構建的積極性是很高的。比如,一些國家組建中等國家聯盟,發揮特殊的參與和平衡作用,一些區域組織也積極發揮作用,對於中美兩國,也不想選邊站,這就為權勢轉移提供了運作空間與緩衝地帶。
當然,美國和中國需要進行自我調整,既要調整認識、理念,也要調整行為。正如有的美國專家所說,美國人也要明白,美國並不理所當然地領導世界,美國必須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轉變。當然,對於美國來說,理性地接受權勢衰落和轉移也難,一些極端的行為也會發生,重要的是防止引發“群動”,或者說是集團性對抗。對於中國來說,需要考慮和平崛起的綜合影響,增加自身戰略與目標設定的透明度和相融性。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讓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以避免引起戰略誤解與誤判。作為一個復興的大國,中國期待立於世界舞台中央,但也要清楚,屆時立於世界舞台中央的不會只有中國,還會有他者,這是新時代權勢轉移的一個突出特徵。
儘管如此,面對過渡期的不確定性,人們還是擔心如何應對權勢分解與分散出現的亂局和沒有大國霸權的“無序世界”。其實,如今的世界還是有基礎秩序根基的。聯合國的建立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幾乎所有國家都參與其中,其主要功能是規定了國家間相處的基本原則,建構了維護世界基本秩序與和平的治理機制。
我們看到,儘管美國政府把中國說成是最大的“威脅”,不遺餘力地拉攏其他國家、組織圍堵中國的聯盟,實際上真心跟隨者寥寥無幾。很多國家也許擔心中國崛起,在防止中國一家獨大上有一定的圖謀,但在與中國對抗,甚至參與與中國打仗上還是慎之又慎的。當然,美國還有軍事同盟體系,以往,盟國也以各種方式協同美國的行動,但是,在新時代權勢轉移上,願意為美國稱霸而戰者恐怕不多。至於中國,為了自己的發展,不會為獲取主導權勢而發起對抗。不爭霸、不稱霸,誓做新型大國,是中國對自己、對世界的莊嚴承諾。
儘管新時代權勢轉移的內涵和方式發生了變化,出於權勢的慣性,在實力對比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基於維護利益的考慮,也會形成激烈的競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競爭優勢,各方特別是原來擁有優勢的一方,可能會採取一些極端的措施,特別是為了維護高技術的競爭優勢,會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與遏制。但是,與勢不兩立的對抗不同,只要不關閉大門,競爭下的聯繫與合作空間還是存在的。在這個大變局的時代,不能僅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基於歷史經驗的認定來看待和對待當今權勢的轉移,新時代呼喚新的理論、共識、行動和角色。
四、謀劃未來的思考
謀劃未來,當然首先需要考慮中國的發展,基於中國的利益來確定大戰略。中國的大戰略是甚麼?簡單地說,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通過自己的成功與影響力推動世界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實現中國夢,當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在一個開放和相互依賴的世界,實現自身發展的成功必須對接世界,對外開放,有效應對變化的外部環境挑戰,要主動和有能力抓住並利用好機遇。同時,作為一個大國,需要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非同一般的貢獻。
從時代的視角來看,世界處於一個大變局時期,大變局的最突出特點是世界權勢格局的結構與內涵發生重大轉變,由一個大國或者少數幾個大國掌控世界的格局,向一個基於多元化、多樣化的世界格局與秩序轉變。這個歷史轉變進程會很長,但是大趨勢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對於中國作為復興大國爭取發展空間、發揮新型大國作用總體上是有利的。這與歷史上總是由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爭奪、以戰爭決勝負的所謂“歷史規律”,或者兩國陷入決鬥陷阱的慣例不同,也與權勢的轉移總是由一個大國傳遞給另一個大國的範式有別。
以多元化、多樣化為主要特徵的新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構建,需要基於不同的戰略思維與定位:其一,推動基於共同參與的國際治理機制構建,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治理體系基礎,改革現有的基於權勢決策的架構,構建更為公平合理和有效率的國際治理決策方式。這裏,既需要體現合理,也需要體現效率,實現包容與效率二者的有機結合。其二,發揮大國引領的作用,通過提出動議、倡議和提供具體承諾等,發揮大國負責任的導向或者領導作用,為各方提供競爭與合作的環境,即鼓勵和支持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防止我行我素的單邊主義。同時,積極促進多角色的參與和能動性發揮。當然,向新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的演進充滿風險、充滿爭鬥,因為涉及權勢、地位、利益等博弈。因此,歷史轉變的進程也許會有很大的波折。
為了體現並發揮復興大國、新型大國的作用,中國作出了許多承諾,最為重要的承諾是“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中國也提出不少倡議並加以實施和推動,比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領銜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隨着綜合實力和能力的提升,中國還會做得更多。中國的作為並非要另起爐灶,自行構建一個全新的替代性體系,而是旨在推動現有體系的變革,構建一個以現有體系為基礎、面向未來、具有新內涵的開放和包容體系。
其實,就中國自身而言,同時也是他者的期待,要對兩個大的問題作出明確回答:其一,中國會是一個甚麼樣的復興大國?儘管中國做出了承諾,“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並且一再表明堅守承諾,但對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外部世界很多人還是帶着懷疑的眼光,對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表現出驚恐、警惕和不信任。其二,中國會扮演一個甚麼角色?追求甚麼目標?中共十九大對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有明確的定位:“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所追求的目標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儘管如此,鑒於歷史上沒有一個復興大國有這樣獨特的定位和目標設定,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此多有懷疑。因此,一則需要中國言行一致,二則也需要世界為中國提供發展和發揮作用的環境,增進對中國的信任。事實上,在大變局時期,取信是一個基於時間和實踐的相互磨合的過程。
就世界的發展來說,人類處在一個向新文明轉變的重要歷史時期,這也是大變局的最深刻含義。回顧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工業革命時代代替了農耕時代,推動了人類走向工業文明。然而,工業文明伴隨帝國主義、擴張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在為世界創造福祉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比如,殖民主義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蹂躪,帝國爭奪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資源過度消耗帶來的生態危機,溫室效應導致的氣候變化等,讓地球生態與人類生存付出巨大的代價,到了進行根本性轉變的時候了。
當然,向新文明轉變是一個長歷史進程,不像以往帝國爭霸,勝者為王,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新文明的構建是靠多數國家的共識與協同共進來推動的。在這個過程中,舊與新、挫折與前進、分歧與共識、爭鬥與合作並存,既充滿機遇,也充滿風險。因此,百年大變局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需要把握大的方向,推動大趨勢向好的方向發展。
中國作為新型大國,在推動改變、構建人類新文明上肩負責任。中國本身的發展有諸多困難,也存在可能影響行進方向的問題,比如,如何不讓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失控,如何處理敏感且極具危險的台灣問題,如何與時俱進確保自身發展的可持續性等,解決這些問題並非易事。然而,對中國來說,維護復興進程的有利國際環境,開拓發揮新型大國作用的空間,推動世界向容納新文明的新秩序轉變,是最為理智的定位和選擇。
張蘊嶺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