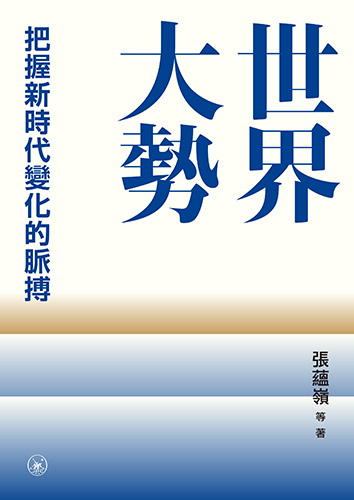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
簡介
何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什麽、怎麽變、變到哪裏去?本書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了戰略性和全面性的研究,系統總結和專業解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麽,如何應對全球之變、地區之變、中國之變等難題,並提出一系列創新理論和戰略對策。
本書特點:
★把握國際變局新動向,應對國內治理新問題
★貢獻中國智慧,回答“世界向何處去?”
★多角度探尋世界變局下的中國應對之策
★十餘位國際問題專家縱論百年大變局
★內容豐富,語言通俗生動,可讀性强
目錄
序言i
大變局中的世界秩序/金燦榮 郭振家001
一、西方引領下的全球化001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005
三、世界秩序面臨新的演變008
結語012
大變局中的美國/倪峰 魏南枝 齊皓013
一、經濟之變014
二、社會之變021
三、政治之變027
四、外交之變032
結論:美國是當今國際體系變動最顯著的變量039
歷史上的“百年大變局”及演變動力/朱鋒 周嘉希041
一、回溯近代以來的“百年大變局”041
二、百年大變局的動力探索056
三、新環境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064
大變局中的世界經濟/沈銘輝 秦升067
一、預測未來:變局大勢067
二、綜合實力對比之變070
三、多邊貿易體制改革074
四、區域化發展大勢077
五、全球化和價值鏈之變081
六、新科技發展大勢與影響084
七、全球治理的困境088
八、選擇:和合共生091
大變局中的世界政治/楊光斌095
一、國際關係重塑095
二、世界秩序之變097
三、現代世界體系098
四、現行世界秩序的演化101
五、大變革中的世界秩序103
六、世界秩序的價值觀107
七、新世界秩序願景112
八、呼喚世界政治理論114
世界政治大變局中的民粹主義/張國璽 謝韜116
引言:重新認識民粹主義的“幽靈”116
一、理解民粹主義的多重面相:上下之爭與左右之分117
二、變化中的民粹主義譜系:從地區到全球的新特徵121
三、民粹主義崛起的再解讀:從物質到身份127
四、民粹主義的政治邏輯:政黨、政客與選民130
五、大變局中的民粹主義:全球化、國際秩序與西方民主135
六、西方民主的民粹主義選擇:飲鴆止渴還是刮骨療傷138
結語:民粹不會消亡,歷史遠未終結141
大變局中的周邊格局/鍾飛騰143
一、周邊關係歷史大變局143
二、周邊關係再變局149
三、周邊政經新格局155
四、周邊地區新發展158
五、中國的周邊新戰略162
結語168
大變局中中國的世界定位/魏玲171
引言171
一、美國的百年變局運籌173
二、百年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178
三、百年大變局下的國際秩序184
四、中國與國際秩序塑造188
大變局下的中國外交/任晶晶198
一、大變局帶來大機遇199
二、大變局帶來大挑戰201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3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下的中國外交208
五、中國外交的創新性實踐211
六、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18
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唐永勝221
一、理解和認識國際大變局222
二、大變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226
三、應對複雜多變的新局勢231
四、拓展戰略空間,提升戰略能力237
作者簡介
張蘊嶺
男,1945年5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安全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國內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曾獲“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是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東亞展望小組成員,中國—東盟合作官方專家組成員,亞歐合作專家組亞洲代表成員,東亞自由貿易區可行性研究專家組組長,東亞經濟夥伴關係可行性研究專家組成員,中韓聯合專家委員會中方主席,中韓友好協會副會長,德意志銀行亞太地區顧問等。
主要代表專著有:《世界經濟中的相互依賴關係》、《未來10—15年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中國與亞洲區域主義》(英文)《世界市場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與世界:新變化、新認識與新定位》《構建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尋求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等。
序言
百年大變局,變什麼
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回國參加2017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全體使節時的講話中提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8年6月23日,他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他又提到“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何一再提“百年大變局”?對於“百年大變局”的含義究竟如何認識?如何把“百年大變局”放在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視野下進行認識?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百年大變局,從字面上理解,百年,是指一個長時期的跨度,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大變局,是說發生重要的、影響巨大的變化,不是小規模、局部的改變。既然是變局,也意味著變化涉及大的格局、秩序、體系。因此,對於百年大變局,要有歷史的眼光,有大視野,有謀略。“百年大變局”的關鍵字是“變”,要研究變什麼、怎麼變、變到哪裏去,對“變”也要分層次、分視角。從範疇方面說,可分為全球之變與中國之變;從內涵方面說,可分為權勢之變與秩序之變;從領域方面說,可分為政治之變、經濟之變與社會之變。
從視角定位來觀察,具有大視野的方法是圍繞新千年的上下一百年,即上個百年和這個百年來觀察中國與世界。以這樣的時間坐標來觀察和認識,上個百年就是從1900年至2000年,即20世紀;這個百年就是從2000年到2100年,即21世紀,由此,也可以稱之為“世紀之變的認識與觀察”。這樣定位的基本考慮是,這期間是世紀交替和新千年轉換,一般來說,世紀交替和新千年轉換期往往是大變局時期。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個時間定位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時期發生的變化和將要發生的變化不僅深刻,而且深遠。中國的近代衰落和現代復興都與世界大變局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中國與世界的變局是同步交織與相互作用的。
當然,也可以有其他方法,比如,以現代中國為中心視角的世界大變局,可以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1世紀中期的百年大變局。從世界觀察,可以重點考察二戰以後的變局,從世界制度構建到發展調整。從中國觀察,可以考察中國從弱到強的轉變進程。比如,以美國霸權的形成與衰落為中心視角的世界大變局,可以從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霸權逐步確立,到逐步“力不從心”,主動或者被動減弱霸權地位的大變局,以及由此相連的諸多變化。這樣的觀察和研究還可以用於對各個不同領域的研究,比如經濟、政治、國際關係、社會、文化、科技,等等。每一個領域的大變局都會引起其他領域的變化,並且與其他領域相聯繫。
不過,任何大變局都是由小變化逐步累積而成的,由量變到質變,因此,研究大變局不可忽視小變局,甚至是微變局。觀察和研究這些“細小的變化”,往往可以從中發現大趨勢變化的內在根源。
“歷史是一面鏡子”,審視這個百年之變,有必要對上個百年,即20世紀,做一些回顧和分析,且從世界與中國的“兩者同步交織”的視角來進行。
一、上個百年的世界
20世紀是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看,大變局都是前所未有的,總的特點是:在世界秩序方面,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世界建立了基本的國際關係秩序規則;在經濟發展方面,基於開放的秩序,全球化得到擴展,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20世紀之初,歐洲列強爭奪激烈,結成相互對立的集團,一場大戰終於在1914年爆發,很快很多國家被捲入,成為一場慘烈的世界大戰。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打了4年,有6500萬人參與,死傷2500萬人,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損失巨大。
1917年,世界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即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場革命的意義遠遠超出俄國,因為它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一大批國家建立了由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權,並且以蘇聯為首結成了強大的“東方集團”,形成了東西方對抗的冷戰,把人類帶入前所未有的核戰爭危局。
1929年,一場未曾預料到的經濟危機爆發,從美國到歐洲,整個工業化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蕭條,工廠、銀行倒閉,工人失業,就像一場浩劫,持續了將近5年的時間,儘管危機到1933年基本結束,但是,此後幾年世界仍然籠罩在陰影之中。由於危機的影響,美國、英國都先後宣佈終止一戰以後建立的金本位制。
危機的創傷尚未完全治癒,另一場劫難又開始了。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此次大戰先後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多億人口被捲入,遍及世界各大洲。戰爭中,9000餘萬人失去生命,其規模和損失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1945年才結束。
二戰後,開啟了新秩序構建的進程。在戰爭還未結束的時候,1942年1月1日,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聯合國。1944年7月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簽訂。這一時期,還先後成立了16個聯合國專門機構,涵蓋經濟、社會、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領域。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的建立是世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戰後,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終結了西方列強建立的殖民制度,讓各國獲得了獨立,先後加入了聯合國,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鑒於幾乎所有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大多數國家加入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其他國際組織,由此,可以說世界進入了以獨立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新時代。
不過,世界出現了新的分裂。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對立形成了冷戰,讓剛剛從世界大戰的廢墟中走出來的世界又陷入分裂與核恐怖的陰影之下。冷戰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990年才結束。冷戰以非戰爭的方式結束,這使世界獲得了“和平紅利”。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自我膨脹,力圖憑藉霸權創建“美國治下的和平”,構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其結果是激發了新的矛盾,引發了暴恐勢力興起,讓世界陷入新的威脅之中。
總的來看,二戰後儘管世界並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穩定的金融體系,開放的世界市場,新的科技革命興起,全球化深入發展等,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被稱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大格局——發展中國家經濟所佔比例大幅度提高,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
20世紀最重要的變局是,在二戰以後開啟了世界秩序的重建,正是二戰後的世界治理,避免了新的大戰發生,讓世界得到新的大發展。在20世紀的變局中,最應記取的教訓是什麼、經驗是什麼?就世界秩序而言,最應記取的教訓是,大國爭霸,後起新興大國爭奪,以及霸權國家推行霸權政策,導致戰爭與對抗,而結夥、結盟對抗會引起更大的衝突,對人類造成災難。最重要的經驗是,世界治理需要廣泛參與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合作組織與機制,合作安全、合作發展才能實現和平與發展的可持續。
二、“沒有答案”的21世紀
2000年標誌著人類進入新的千年,也開啟了21世紀的進程。迄今,新世紀尚不到20年,一些變局的大趨勢已經顯現。但是,面對新的變化,人們最為關心的是,未來的世界將會如何。樂觀者認為,這個百年是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的構建期;而悲觀者則預測,世界可能會重新進入類似20世紀的大國紛爭與戰亂;懷疑論者則提出,未來是一個“沒有答案的世界”。
新世紀大變局的最重要體現發生在處在霸權頂端的美國。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恐怖襲擊,一架民航客機撞擊紐約世貿大樓,頃刻間,大樓傾塌,大批人員傷亡,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也遭到恐怖襲擊。“9.11”恐怖襲擊事件促使美國發起世界範圍的反恐戰爭,2001年10月7日,美國派兵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權。美國動員北約及其盟友參加阿富汗戰爭,最多時,派兵多達15萬人。直到2014年底,美國才宣佈阿富汗戰爭結束。不過,至今仍有美軍駐留在阿富汗。戰爭奪去10多萬阿富汗人、2000多名美國士兵的生命,直接耗資近萬億美元。儘管美國已宣佈反恐戰爭結束,但是,恐怖主義勢力在一些地區仍然猖獗,美國以反恐為名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恐怖主義的起因複雜,從直接的原因看,與冷戰結束後美國霸權膨脹,在世界強行推行“美國式秩序”不無關係。伊拉克戰爭激化了中東的宗教矛盾,打開了恐怖勢力的魔瓶蓋子,助長了恐怖主義勢力的興起。有的人認為,“9.11”恐怖襲擊事件是極端勢力對美國強制推行“美國式秩序”的一種反抗,也是一種“警告”。也有的人認為,“恐襲”是美式霸權由頂峰開始跌落的一個轉折點。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很快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和全面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影響巨大而深遠,迄今還被認為是在後危機的調整時期。這次危機被認為是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以來的最嚴重危機,此言並不為過。從直接的原因看,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美國金融本身出了問題,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由於缺乏有效監督,金融衍生產品過度膨脹,導致金融市場發生信貸危機,但從世界範圍來說,則是經濟結構大失衡的結果。鑒於此,後危機的調整與恢復才變得如此困難。後危機時期的矛盾增多,標誌著全球化下經濟的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從大變局的視角來分析,則反映了美國經濟霸權的轉變,而這正是美國特朗普上台執政,推行單邊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的內在原因。“美國優先”政策意味著美國以推行市場開放為目標的多邊主義政策發生逆轉,同時也反映了在全球化環境下,美國參與開放競爭能力的下降。回顧上個百年,1970年初美國放棄自己確定的美元—金本位體系,表明了美國已無力承擔充當世界貨幣保證人的角色;而如今,美國更是不再承擔世界開放的責任。
迄今,初露端倪的百年大變局大勢,不是突然冒出來的,皆為長期量變的積累。究竟如何發展、結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一)權勢對比的變化
按照綜合預測,這個百年前50年的最大變化,就是世界權勢對比的大變局。這裏,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觀察和分析力量對比的大變化。
其一,自西方開啟工業化以後,世界的權勢重心向西方轉移,從歐洲到美國,由此,世界分為發達國家群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曾佔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的80%。如今,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GDP佔到5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根據預測,到這個百年的中期,經濟總量將可顯著超過現有的發達國家。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觀察,拉動力,或者說是增量部分可能主要來自現有的發展中國家群體。這將會是當代史上世界發展的一個重大轉變。
其二,從國家權勢的角度看,在21世紀上半期,最有可能轉變的是中國的綜合力量超越美國,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進入前三。這樣,就綜合國力而言,排在前三的國家可能依次是中國、美國、印度,而老牌的歐洲國家大多被擠出前五位。從大國的屬性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國家中,有兩個是非傳統西方大國,這無疑是自西方工業化以來最重要的權勢格局的轉變。
如果是這樣,從各個方面來說,其影響都是巨大的。值得深入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多樣性群體崛起,究竟如何引導世界的變化?儘管在現有的發展中國家群體中,有些會躍升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群體內差別也很大,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它們與傳統的西方群體有著很大的不同。儘管如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加入了一個共處的國際體系,後起者並不要求“另起爐灶”,推翻現行體系、制度,但必定會推動其調整與改革。新的體系與規則構建必須能更好地體現後起者的利益訴求和能為它們提供可發揮作用的空間與平台。
從這個視角觀察,儘管維護現有體系是一個共識基礎,但調整與改革是必須進行的。從好的方面說,如果能實現合作,則世界會走出你死我活的“叢林法則”,共建一種包容共處的新文明。如果不能達成共識,則會出現衝突和對抗,甚至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即便是有共識,涉及體系和規則的調整與改革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作為原有體系與秩序的主導者,肯定會力圖保住自己的利益,由此會引起衝突。從歷史的發展看,權勢的根本性轉變會需要很長的時間,也許21世紀的轉變只是序曲。
從以往的歷史看,權勢轉變會發生大的動盪、大的戰爭。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講的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上個百年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國挑戰既有世界秩序,結果引起兩次世界大戰;下半期,主要是美蘇爭霸,發生了長達幾十年的冷戰。這個百年,難道是中國與美國的對抗嗎?儘管中國有可能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但中國會全面挑戰既有世界秩序,替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嗎?這當然是世人極為關注的大局。
權勢轉變的最大影響是導向問題,世界未來的發展會是由傳統的西方導向轉為“非西方導向”嗎?歐洲工業化以來,主要是西方導向,包括發展範式、價值觀、國際關係理論等。所謂“非西方導向”的含義是什麼?會不會改變非此即彼的傳統範式,發展新的範式呢?
權勢轉變必然會導致傳統的霸權衰落。儘管人們對霸權秩序很不滿意,但對大國爭霸深表擔心,對“無霸權秩序”也充滿疑慮。從以往的歷史看,霸權的確立總是需要經過戰爭,無論是把挑戰者打下去,還是挑戰者勝出,都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特朗普上任後打出“美國優先”的旗子,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通過一系列戰略與政策保住美國的霸權地位,為此不惜打貿易戰,退出國際組織,終止原有的條約,對認定的競爭對手——主要是中國——採取制裁、施壓、封堵等一系列措施,極具對抗性。這無疑會挑起一系列的矛盾,甚至發生對抗。面對這樣的形勢,人們發出疑問,未來的世界會發生類似上個百年的大戰嗎?能否以“非戰爭方式”走向人類新文明,實現“霸權的終結”呢?這些都是這個百年大變局繞不開的大議題。
(二)發展範式的危機
西方創造了工業化模式,推動了世界的大發展,讓更多的國家步入了工業化行列。現在這個追趕型現代化模式出現了各種問題,遭遇了綜合性危機,包括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等等。傳統工業化發展的基本特徵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為目標,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工業化進程,產品的生產和對產品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多,事實表明,這種範式難以為繼,因此,出現了“發展範式”的危機。
財富的分配也出了大問題。全球化創建了世界市場與國際生產網絡,讓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流動與佈局,由此極大地拓展了經濟規模效益,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但是,在一個開放的大市場空間,財富積累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也使得許多地區因“沒有競爭優勢”而變得“空心化”,使許多人,甚至國家被邊緣化,從而導致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現實中,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反全球化的勢力、民粹主義勢力,以及極端勢力也在滋長,甚至形成很強的政治勢力或具有跨國特徵的集團。如今,世界的相互連接越來越緊密,這些問題與其他問題交織,形成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
世界需要新的發展範式。但是,發展範式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進程。西方工業化範式延續數百年,幾乎所有的進步、財富積累、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取向等都是以其為基礎,受到其導向的。因此,轉變並不是完全拋棄原有的,而是對其進行修正與改進。特別是傳統的利益集團會拚力保護舊範式,許多落後的國家或地區也許缺乏轉變的能力,要麼被舊範式拖累,而落後於時代;要麼被再次邊緣化,進而引起矛盾或者衝突。
重要的是,新發展範式是一個不斷蛻變的創新過程,就生產而言,生產的內容不斷發生變化,效率不斷提高,向社會的供給不斷創新,從而創建基於新範式的可持續發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費模式會發生變化,更少的物品消費,更高的生活質量,從而創建以人為本的新理念。這個百年是轉型期,既有痛苦的,也有幸福的,也許在很長時間內仍沒有清晰的答案,但大勢所趨,沒有回頭路。
(三)氣候變化的未知性
氣候變化是這個百年最具影響的大變局,因為它會影響整個人類的基本生存環境,帶來巨大的未知性。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調查,在被訪問的兩萬多人中,大多數人把氣候變化作為頭等威脅。據研究,到21世紀中期,即2050年,如果繼續現在的趨勢,不能控制住氣溫升高,那將是災難性的。
氣候變化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與傳統的生產方式有著極大的關係,也與人類生活方式有關。有證據表明,地球生態系統和地球氣候系統可能已經達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臨界點,可能導致不可逆轉的變化。聯合國早在上個百年就開始採取應對行動。199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公約,即《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先後有196個國家簽署了該公約,一致同意承擔責任,採取共同行動,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防止發生危及人類生存的氣候變化。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先後有183個國家簽署,議定書旨在落實公約的具體責任與承諾至2020年的行動議程。2015年底,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巴黎協定》,在《京都議定書》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安排。這三個文件是人類史無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諾。
不過,由於各國利益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落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安排並非易事。本來,美國、加拿大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後來都先後宣佈退出。美國曾是促使《巴黎協定》簽署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後宣佈退出,他甚至明確表示,不存在氣候變暖,是言過其實,不為減排買單。特朗普是真的不信,還是為了“美國優先”另有圖謀?
氣候變化危及人類生存,防止悲劇發生是各國的共同責任和義務。美國、加拿大,特別是美國的退出,不僅自己不盡責,而且也產生了極壞的影響。事實上,氣候極端變化的趨勢還在發展,南北極冰川的融化、喜馬拉雅山冰川融化,氣候極端化的加劇所造成的綜合影響將會進一步凸顯,未來的變化令人們越來越擔心。氣候變化危及人類生存,國際社會必須重聚共識,聯合國安理會應該把應對氣候變化列入議程,畢竟所涉及的是人類的共同安全,因此,各國也就有了共同的責任。不過,在氣候變化的“灰犀牛”衝到人類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還不相信“人類悲劇”真的會發生,也有很多人試圖置身事外,逃避承擔公共責任,這也許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
(四)新科技革命的“風暴”
我們正處在一場新的科技革命之中,它剛剛開始,就顯示出驚人的創造力了。以智能化技術為牽引的這場新科技運動,猶如一場“風暴”,席捲各個領域,預計會在21世紀的前半期得到廣泛應用。智能化與以往的科技革命技術不同,是以模擬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變人的智能為特徵,把智能應用到廣泛的領域,從而開啟發展的新境界,造成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的大變局。
從以往的發展看,新的科技革命總是會推動新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這場新科技革命的深入發展會催生新的經濟領域、新的經濟運行方式,從而使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發生革命性的變革。智能化不僅創造更高的效率,而且創造更新的方式。鑒於此,樂觀者認為,傳統生產方式所存在與積累的問題也可能會得到緩解,甚至得到解決。比如,廢氣排放問題,智能化可能會使得能源利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等等。
對於本書的分析來說,我們更關注的是智能化技術的深入與廣泛應用對世界變局所產生的影響。一方面,智能化發展是打造新競爭優勢的關鍵,而智能技術的開發利用更會向少數國家與公司集中,因此,新一輪科技革命會改變現有的競爭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化技術會比以往的自動化技術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國家的地區與全球網絡,因此,會把更多的國家吸納進網絡圈,從這個意義上說,智能化會進一步推進全球化的發展。在智能化風暴面前,國家政策選擇可能會出現兩種大趨勢:一是技術壟斷或者技術封堵,以便可以佔據競爭制高點,排斥競爭者。當前,特朗普政府便是這樣做的,誓言美國必須成為第一,為此對其他競爭者,特別是中國進行技術封堵。二是推動開放,構建合作網絡,打造基於區域和全球市場的開放網絡空間,把盡可能多的國家或者公司納入一個網絡之中,而對於不具備開發和利用能力或者優勢的國家或公司來說,加入網絡是最可行的選擇。後起者往往更支持這種開放發展與合作參與的選擇。
以智能化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會帶來很多新的挑戰,比如,智能化會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業化”趨勢,智能化技術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對改變人類基因的濫用,智能化武器與戰爭),等等。鑒於新技術具有很強的超國家特徵,如何凝聚國際共識,制定具有法律約束的國際規則和建立國際監督與執法機構,都是新課題。
總體來看,我們所處的這個百年世界大變局將是深刻的,涉及政治、國際關係、國際秩序、發展範式、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價值觀等。如今,我們正處在世界大變局的初始期,由此,對於未來,還很難描述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似乎是一個“未知的世界”。
在諸多變局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國際秩序的轉變。慕尼黑安全會議(以下簡稱“慕安會”)2019年2月發佈的年度安全報告指出,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版圖正發生劇烈變化,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慕安會”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提出,我們這代人似乎正在經歷國際秩序核心部分的重組。他同時還指出,“危機就在於舊世界正在死亡,而新世界無法誕生,在這個過渡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症狀就會層出不窮。” 他所指的“國際秩序核心”“舊世界”是什麼呢?是指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一家獨大的大格局嗎?而“新世界”又是什麼呢?就期盼而言,當然不是一個戰亂的時代,不是又發生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結局。那麼,“新世界”會是一個人類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秩序嗎?這無疑是一個“百年之問”。
三、百年大變局中的中國
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綜合力量最強的國家,是東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來,面對西方世界的崛起與擴張,中國衰落了,受到了列強的欺凌與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止了中國的下行,開啟了民族復興的進程。到這個百年,即2000年之時,就經濟總量而言,中國重新列於世界大國之林,此後,復興的進程加快,預計到這個百年的中期,即2050年,中國將可望在綜合實力上居世界首位。這個大變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意義非凡的。
(一)20世紀的中國
20世紀對於中國來說,既是悲慘的百年,又是奮爭的世紀。一般認為,中國近代衰落的一個轉折點是1894年,是年,中日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大清朝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向日本賠款和割讓台灣島。若從中國與世界關聯的大視角看,1900年更具深刻的含義,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大清朝統治者倉皇出逃,最後不得不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向列強賠款本息高達9.8億兩白銀(庚子賠款),從此,中國的衰落加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次年建立中華民國,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不過,中華民國成立並沒有為中國開創一個新的時代,軍閥混戰,內亂不止,在日本威逼之下,不得不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1931年,日本關東軍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開始在中國東北擴張,先後侵佔了整個東北三省,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1937年,日本製造了盧溝橋事變,開始進犯全中國,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日本侵略佔領中國達14年,戰爭期間,中國死傷人數達3500多萬,財物損失不計其數。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本侵略者被趕出中國。不過,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發生內戰,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陸才實現穩定,開啟了國家重生、重建的新征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現振興的進程並不順暢,很快就被捲入冷戰的旋渦,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戰爭打了兩年多,中國參戰人數多達百萬以上,死傷人數甚多,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此後,儘管中國不再有外敵入侵的威脅,但外部綜合環境並不好,先是被裹挾在冷戰的旋渦裏,後又與蘇聯交惡,甚至發展到大對抗,不得不“深挖洞,廣積糧”,準備“背水一戰”,與印度、越南因邊界爭端發生戰事……,也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內亂。直到1978年中國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內外環境才開始發生巨變。改革開放真正改變了中國,讓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裏實現了發展上的騰飛,同時也找回了中國失去的尊嚴。到200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1萬億美元,進入世界強國行列。
縱觀中國上個百年的歷史,從衰敗到重生,重要的啟示是:其一,國之衰,內因是主要的,清朝晚期已是病入膏肓,窮途末路,積重難返,謀求變革的維新運動所點燃的一點火花也被撲滅。中華民國的成立曾為中國走出困境帶來希望,但是,在外敵入侵面前卻是連連敗退,國之不國,令人痛心疾首。其二,改革開放讓中國迅速從一個貧窮的國家躍升到世界前列,主要的原因是對內改革僵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對外向世界開放,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把中國與世界聯結起來,形成了良性互動。世界都仰慕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奇跡,在短短幾十年間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轉變。
(二)21世紀的中國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一個帶有轉折意義的變化,它代表著中國“回歸國際社會”,加入現行主流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還有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以單獨關稅區的名義一起加入),與國際接軌。也許有人說,中國加入WTO的條件太苛刻了,談判進行了15年!其實,這個過程正是中國痛下決心,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與國際市場經濟對接的過程。對接為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加快發展,並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談到中國之變,一個不能不提的大事件是2008年中國舉辦北京奧運會。本來,奧運會就是一場世界性的體育賽事,對中國來說更是非同一般。中國把舉辦奧運看作一個歷史的機遇,204個國家和地區參會,80個國家領導人與會,盛況空前。通過舉辦世界盛會,中國不僅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發展成就,而且還可以向世界表明新型大國的價值觀。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含義很清晰,即崛起的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決心為實現和平、和諧與發展的世界做出貢獻。值得提及的是,2008年發生了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國政府立即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推出高達4萬億元人民幣的綜合計劃,不僅保持了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而且成為支持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2010年,按美元計算的GDP,中國超過日本。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變局意義的變化。近代以來,日本通過維新向西方學習,走工業現代化道路,經濟實力快速超越中國,改變了中國作為亞洲老大的力量格局。這個改變導致了災難性後果——日本進行軍事擴張,與西方大國爭霸,力圖建立以己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大半中國被其侵略佔領。二戰後,戰敗的日本很快實現經濟復興,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遠超中國。到2000年,日本的GDP還是中國的4倍多,而僅僅10年的時間,中國就超過日本,到2018年,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2.7倍了。儘管由於人口規模的因素,按人均計算,中國還遠遠落在日本的後面,但就綜合力量格局對比而言,總量的超越是具有特別意義的。
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了明確和具體的規劃目標。按照“兩步走”的進程,到21世紀中葉,即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但是並不是遙不可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顯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這個百年上半期中國的根本任務。
對中國來說,2050年還具有另一層特別的含義。中國語境中的“兩個一百年”,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即2021年,按照既定目標,屆時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即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顯而易見,21世紀上半期是夢想成真的關鍵時期。
(三)中國的“雙重使命”
如果把中國的發展放在世界發展的大視野下來認識,對於中國的百年大變局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因為,一則中國的發展需要外部的環境支持,二則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從中國的角度分析,具有廣域的內容和綜合的含義。
中國對百年大變局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綜合實力的上升、走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上,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以新理念創建發展範式上。中國沿襲傳統發展範式實現了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土地污染等。同時,鑒於中國規模大,與世界緊密連接,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巨大。因此,轉變發展方式,不僅是中國自身最為緊迫的任務,也是世界發展所需。
由此,中國的發展範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使命,既為自己,也為世界。新發展範式需要體現:綠色可持續;新能源結構,突破傳統方式的資源、能源制約;能夠體現效率與公平的基本均衡。也許這個世紀難以完全實現這樣的目標,形成新的發展範式,但至少要有大的轉變,並且能夠起到很好的導向作用。向新範式的轉變是一場大變局,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非常艱難的,並且發展方式的轉變是與政治、社會、文化價值相聯繫的,需要有與此相向而行的政治變革、社會轉變與文化創新。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的發展還處在由低向高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的難度是很大的。為此,中國必須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跳出傳統經濟範式的轉型定式,實現創新型“跨越式轉型”。同時,向新發展範式的轉變不是中國一國的事,而是全世界的事,需要各國的協調與合作,一方面需要創建國際合作機制,另一方面需要各國政府、社會、企業、個人作為共同的利益攸關方承擔責任,並為此制定相應的法規。
中國作為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大國,其轉變的深刻含義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也體現在政治方面。從這方面來說,不僅體現在非西方大國經濟崛起,也體現在非西方大國政治崛起。西方國家堅持西方特色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而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有的人斷言西方價值觀和政治體制將主導世界,由此得出了“歷史終結論”。事實證明,這個論斷並不正確,如今,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發展了現代化政治構建的理論和實踐,並力求把中國長期積累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建設進程結合起來。
在中國特色政治構建的過程中,將會面臨不少挑戰,比如,如何把握經濟社會轉變與政治轉變的均衡,如何建立開放包容的現代政治,把現代、傳統與未來有機結合起來,如何創建多樣性世界的政治共識與協調合作關係等,這些既是對中國本身發展的探索,也是對世界發展的探索,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政治變革要比經濟變革更為複雜,難度更大,因為政治變革是有深刻含義的探索與創新,需要付出巨大的和艱苦的努力。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影響突出地體現在自身發展對世界的作用上。比如,在經濟上,由於規模大,無論是總量的增減,還是單量的增減,都會對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發展的成功是對世界發展的巨大貢獻。在政治上,中國走不同於西方的特色道路,對於多樣性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成功為世界多樣性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每個國家都可以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模式。
其實,中國的政治建設是開放的,是會在進程中不斷進行改革的,“中國模式”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不過,出於對中國影響的考慮,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崛起還是有著很強的政治警覺和抵觸的,並為此採取諸多制約甚至對抗性的措施。同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必然會推動現行國際關係與秩序的變革,包括經濟關係與秩序、政治關係與秩序的調整和變革。但是,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與利益攸關方,自然不會去另起爐灶或者把它推翻,其影響與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通過新的倡議或者行動做出新的貢獻,發揮重要的或者引領性的作用。
(四)推動新型國家關係與秩序
從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來說,權勢變局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正在發生。世界不會是西方一統天下,多樣性實屬正常。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理性的做法是接受世界變化的大趨勢和世界多樣性的現實與未來。不過,現實中,中國的“異軍崛起”還是引起了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警覺,即便中國聲言“不爭霸、不稱霸”,還是被稱為“修正主義者”“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擔心的是中國會引領其他發展中國家“修正”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與秩序,為此,把中國描繪為一個暗藏著推翻西方制度大陰謀的“百年馬拉松”競爭對手。美國國防部前部長馬蒂斯甚至斷定,中國所要構建的是恢復明朝時期的朝貢體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決不能讓中國超過美國。在此情況下,中國看似面臨著要與美國發生“大對抗”的局面。
為了處理好權勢轉變帶來的矛盾,中國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要義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其中,相互尊重是基礎,不衝突不對抗是原則,合作共贏是目的。此前,還沒有一個崛起的大國提出過這樣的原則。為何中國要提出這樣的原則?我看,一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即需要探索一種有別於歷史上大國爭霸、稱霸的傳統關係,避免發生新的戰爭;二是基於中華文明的世界觀,即信奉和諧共處的價值觀,推動新秩序構建。
當然,對中國所倡導與推動的這種新關係與秩序,其他國家並非都拍手稱好。就像美國,迄今並沒有公開支持過中國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在國際關係中,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關係,也是最具風險、最難處理的關係。美國學者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照此理論,中美似乎難以跨越此“陷阱”。現實中,隨著中國綜合力量的提升,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應對越來越具有對抗性。從奧巴馬執政時的“重返亞洲”,到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封堵,有人甚至認為“新冷戰”已經開始。
其實,一個霸權大國不可能永久保持其主導地位,霸權衰落是必然的。歷史的經驗表明,大國興衰的主要原因在內部。在面臨新競爭的情況下,美國盡力維護“美國優先”的地位,並非不可理解,但從發展的趨勢看,採取對抗的方式只能加速其衰落。從這個視角看,美國“退群”、讓盟友承擔更大的責任,也是一種調整。但是,一旦“退群”,不但會失去“道義制高點”,而且還會被“邊緣化”,這也是美國難以接受的。因此,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除了通過談判解決分歧,除了協商合作,好像沒有更好的選擇。
(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會與美國發生對抗嗎?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看看中國是如何定位自己和定位世界的。中國一再宣稱,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老路。冷戰結束後,面對複雜的世界局勢,中國大力推動夥伴關係的構建,與世界各國先後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基本特徵是尋求共同利益,協商合作,結伴不結盟,是在後冷戰時期推動新型國家間關係的創新,也是推動冷戰後世界走向和平發展的重要貢獻。
中國需要也必定會繼續推動現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調整與改革,但不是要當頭兒,不是要另起爐灶。就像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所遵循的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為所有參與方提供開放的大平台,具有特定的地緣含義。對於世界發展來說,“一帶一路”也並不是“萬應靈藥”,而是一種新型的發展合作方式,是一個需要持續投入的“百年工程”。中國要做變局方向的引領者,這個引領本身也是變局的內容,即東方國家在世界發展中的作用回歸。當然,中國要做思想引領者,需要一個開放的思想環境,不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讓人家能進來,讓思想和文化雙向、多向交流,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交往中提升影響力。顯然,百年大變局中的中國、中國與百年大變局,這兩個大課題都值得深度思考,值得深入研究。
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著眼於推動新型國際秩序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涉及全球,具體體現在區域、領域、雙邊與多邊關係各個層次。也許命運共同體的英文翻譯更能體現其內涵——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直譯過來就是“共創未來的共同體”。“共創未來”首先是一個理念,是一種文明,不是一個組織,體現在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從世界、地區到國家,從人類、族群到個人的各個層面。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世界大同”是最高的文明境界。其實,這樣的思想境界也不只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有,比如德國的哲學家康德就提出“永久和平論”等。
新百年需要新理念、新文明。東方文化在推動世界和平、合作、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內容。如今,隨著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復興,曾經對世界文明做出偉大貢獻的東方思想文化,在新的百年大變局中將會發揮自己的引領作用。新百年的轉變是在以往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變局具有連續性,但同時,在新的時代,必定會發生新的改變,會創新方式、關係和秩序。就世界而言,多樣性是一個大趨勢,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不再是由一個霸權國家主導,也並不是由幾個大國可以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多樣性既是一種對現實的描述,也是一種對未來秩序的認定。建立在多樣性基礎上的協商合作,包括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建設,都是不可缺少的。
全球化、新技術變革正在深度改變以往的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基礎與格局,因此,研究和分析新的百年大變局,不能僅僅有歷史的眼光,更要有前瞻的視野,以新的“世界觀”觀察大勢,以新的理念推動未來發展。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