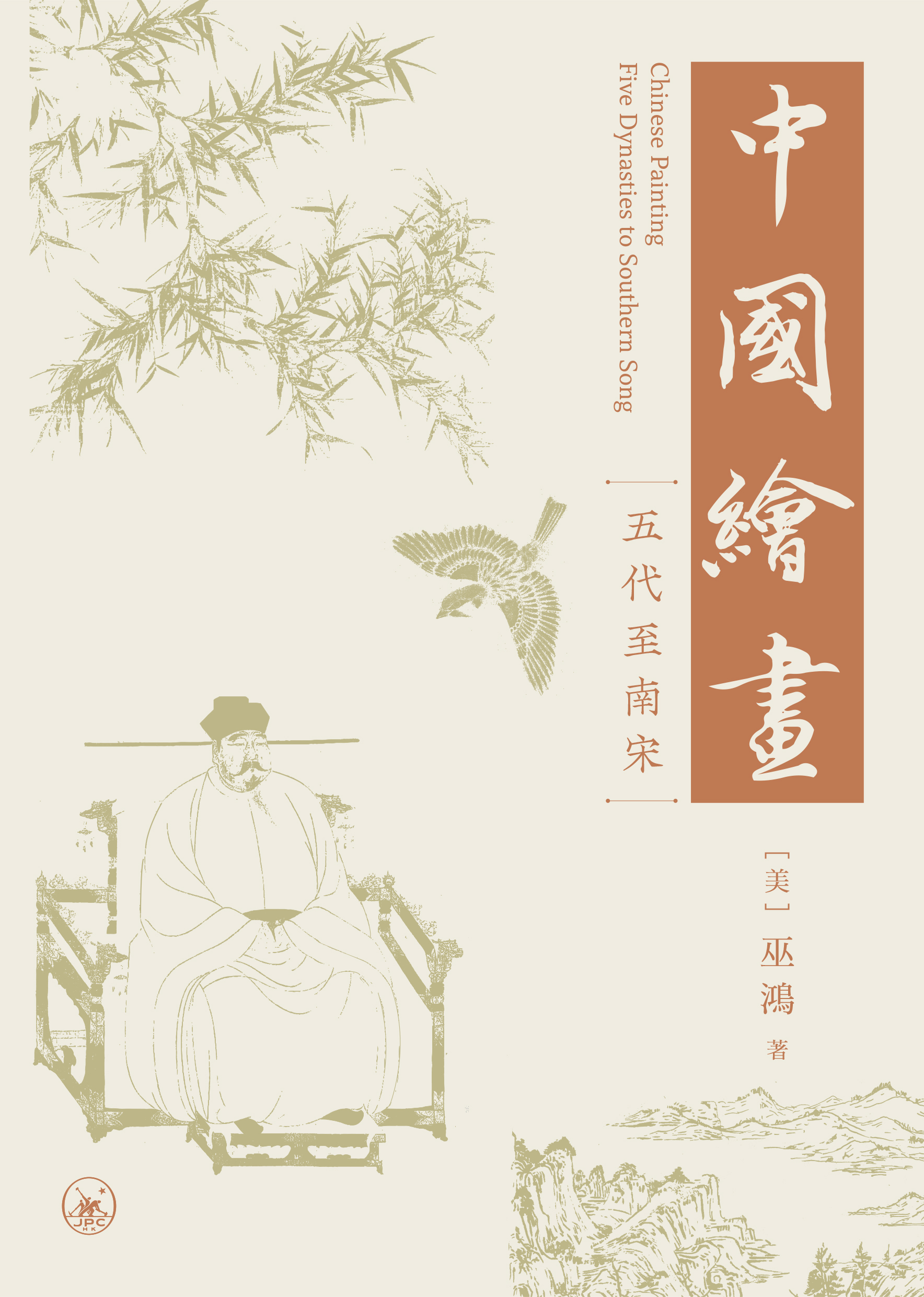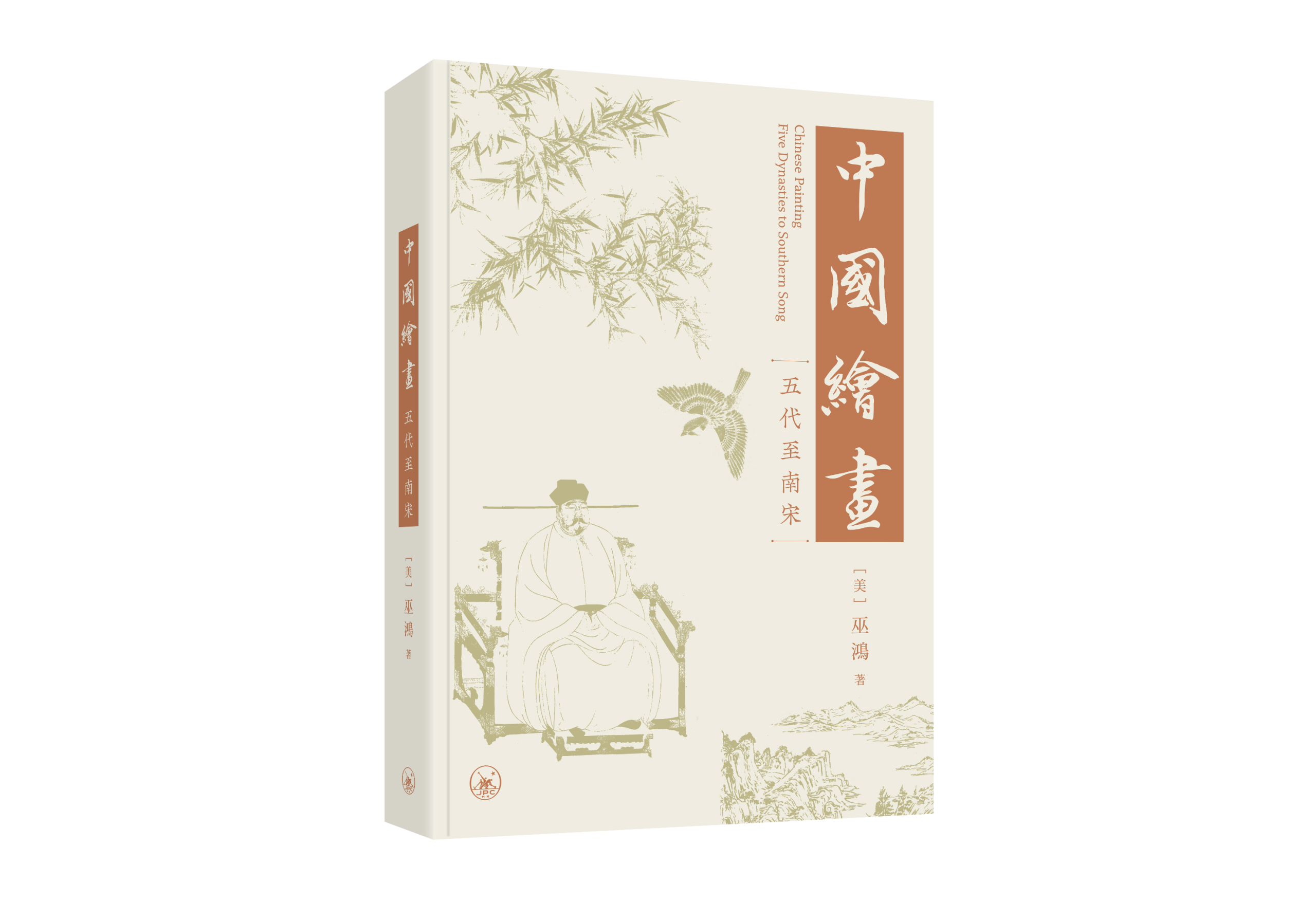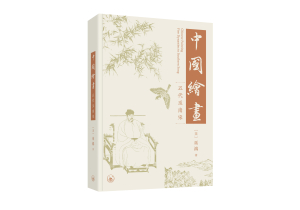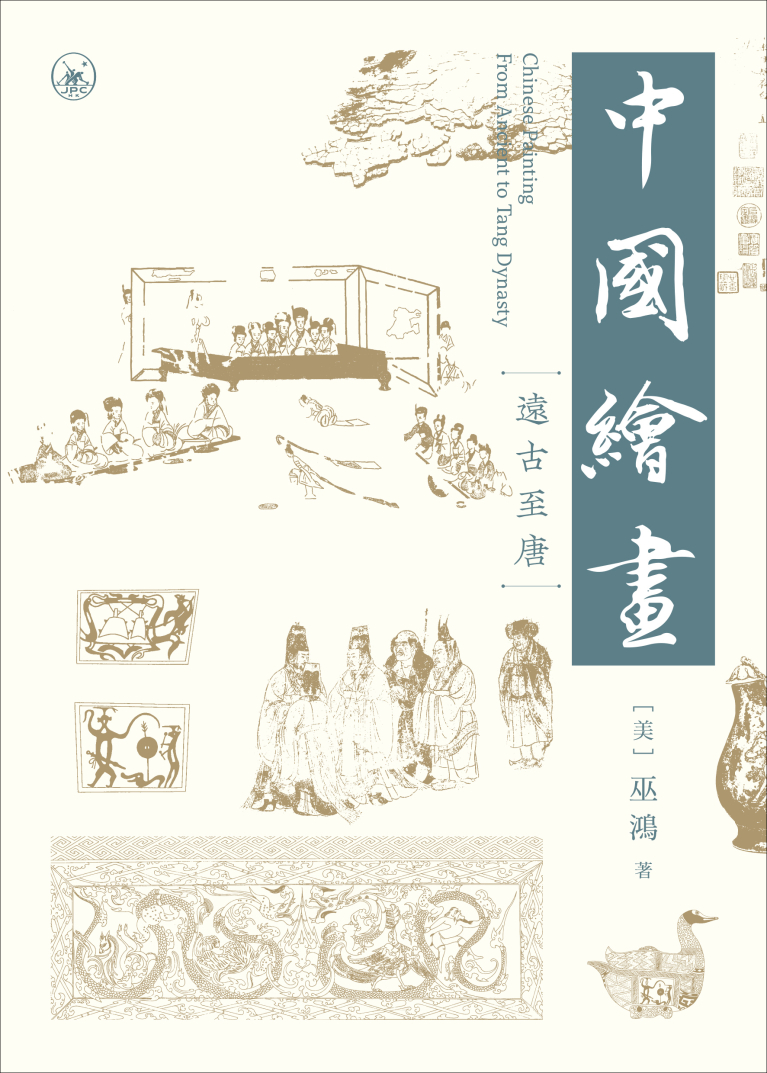中國繪畫:五代至南宋
簡介
五代至南宋這近四百年時間,是《韓熙載夜宴圖》《溪山行旅圖》《千里江山圖》《清明上河圖》等傳世名作湧現的時期,也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個特殊而關鍵的階段:
越來越多的畫家脫離了寺廟和宮室壁畫的集體創作,壁畫與卷軸畫形成新的互動關係;掛軸的產生以及對手卷形式的探索,催生出影響深遠的構圖樣式和觀看方式;日臻細化的繪畫分科隱含著繪畫實踐的進一步專業化;中央及各地方政權的深度參與導致繪畫創作的行政化和機構化,進而形成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綜合性宮廷繪畫系統;孕育中的文人繪畫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其美學觀念影響了宮廷趣味和宗教繪畫的風格,為其最終成為中國繪畫主流開啟了先河。
書是著名美術史家巫鴻的又一力作,延續《中國繪畫:遠古至唐》的寫作思路,吸納考古美術的新近研究成果,聚焦五代至南宋時期各種類型的繪畫作品及其媒材特徵,關注多元背景下的繪畫實踐與跨地域交流,力圖勾勒更加全面、立體的中國繪畫發展脈絡,多維度講述中國繪畫的新故事。
目錄
總 論|001
10世紀:巨變的百年|009
繪畫媒材和圖式的革新 011
畫科的內部發展 033
北宋:宮廷與文人|121
宋初的國家繪畫項目 123
“大山堂堂”圖式 129
宮廷與皇家繪事 150
擴展中的士人影響 180
南宋:融合與流變|217
多維的南宋宮廷繪畫 221
文人趣味的普及 264
人物畫題材的擴展與風俗畫 287
繪畫媒材的小型化 304
跨地域和跨時間的聯結 317
11世紀至13世紀的宗教和墓葬壁畫|335
宗教壁畫 336
墓葬壁畫 348
結 語|374
作者簡介
巫鴻(Wu Hung)
著名美術史家、批評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學教授。
1963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學習。1972—1978年任職於故宮博物院書畫組、金石組。1978年重返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攻讀碩士學位。1980—1987年就讀於哈佛大學,獲美術史與人類學雙重博士學位。隨即在哈佛大學美術史系任教,於1994年獲終身教授職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學亞洲藝術教學,執“斯德本特殊貢獻教授”講席。2002年建立東亞藝術研究中心並任主任,兼任該校斯馬特美術館顧問策展人。2008年被遴選為美國國家文理學院終身院士,並獲美國大學藝術學會美術史教學特殊貢獻獎,2016年獲選為英國牛津大學斯雷特講座教授,2018年獲選為美國大學藝術學會傑出學者,2019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美術館梅隆講座學者,並獲得哈佛大學榮譽藝術博士,2022年榮獲美國大學藝術學會“藝術寫作傑出終身成就獎”,成為大陸赴美學者獲得這些榮譽的第一人。
總論
本卷涵蓋的時期——五代至南宋(907—1279年)——構成後期中國繪畫史的前段,也可說是中國繪畫全過程的中段。如筆者在《中國繪畫:遠古至唐》中提出的,這套書對繪畫史的分期並非建築於朝代史或進化論觀念之上,而是一方面基於繪畫在不同時期的特性,包括其功能和目的、媒材和語彙,以及創作和流通機制;另一方面也根據研究證據和方法的異同。每一時期的繪畫還包含了地域、機構、畫家身份等多條線索。這套書的整體目的是通過發掘這些特性和線索去理解每一時代繪畫的面貌和趨向。
從這個角度觀察五代至南宋這近四百年時間,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無疑構成了一個特殊而關鍵的階段,不論是從繪畫在社會和文化結構中的位置上看,還是從具體創作實踐和理論話語上看,都有別於之前的漢唐和之後的元明清時期,同時又把這前後兩段聯結進一個變化和更新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這一時期繪畫的特殊性格。
首先是繪畫史結構的變化:中國繪畫不再局限於單一政體和社會結構之內。傳統寫作根據朝代沿革把這一時期的繪畫史劃分為分裂狀態下的“五代十國”(907—960年)和隨後建立的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今日的研究者則需要注視更寬廣的政治文化地理空間和更複雜的時間線索,考慮多個政權下的繪畫實踐和藝術交流。繪畫史需要講述一個多元和互動的故事。
這個多元局面從唐代中期之後的藩鎮割據已經開始,至唐代覆亡後遂成為繪畫史的主導,貫穿了1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宋代的統一雖然重建了華夏政治史的正統,但不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這個王朝都和周邊的若干強大政權共存,其中包括10世紀初建立的遼(907—1125 年)和大理(937—1253年),以及11世紀和12世紀出現的西夏(1038—1227年)和金(1115—1234年)。這些政權的疆域往往包含了傳統的漢文化地區。它們與宋緊密接壤,在文化藝術上與宋保持著密切交流,包括藝術家和工匠的流動,以及藝術樣式和風格的傳播。
從繪畫本身的發展來看,這一時期見證了對畫作的重新定義。此前的畫史著作,特別是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和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都證明壁畫和屏障畫是初唐和盛唐畫家的主要用武之處。著名畫家往往有自己的作坊並創造了流行於世的“畫樣”。這種中古時期的繪畫機制在唐代後期開始瓦解:越來越多的畫家脫離了寺廟和宮室壁畫的集體創作,屏風畫和畫幛也越來越被賦予獨立作品的性質。這一趨勢在五代和宋初得到革命性的突破,一個關鍵原因是“掛軸”或“立軸”在 10世紀被發明並得到迅速發展。雖然寺廟壁畫工程從未中斷,屏障畫也仍被大量生產以裝飾宮室住宅,但對富於實驗性和創造性的畫家說來,可攜性卷軸畫提供給他們更為自由的創作平台,刺激他們不斷發明新的構圖樣式和表現方法。掛軸的產生進而促使畫家對傳統手卷的媒材特性進行有意識的發掘,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了影響深遠的新型構圖和觀看方式。
作為中國繪畫史的新階段,這個時期見證了系統的繪畫分科的產生,而畫科的細化又隱含著繪畫實踐的進一步專業化。雖然此前的畫論作者早已提出一些基本的繪畫題材,如傳顧愷之寫的《論畫》中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張彥遠和朱景玄也比較了繪畫題材的高下和難易,但都沒有以此作為劃分畫家、描述繪畫史的首要標準。如《歷代名畫記》以朝代為綱列舉上古至當下的畫家,朱景玄以藝術造詣把畫家分入“神、妙、能”三品。只是到了宋代初年,劉道醇(11世紀中期)才在《五代名畫補遺》和《聖朝名畫評》中提出了明確的畫科分類系統,以人物、山水林木、畜獸、花竹翎毛、鬼神、屋木六門作為建構繪畫史的一級結構。據稱《五代名畫補遺》是10世紀中期胡嶠《廣梁朝畫目》的續篇,雖然胡書已佚,但很可能已經提出這一分類和敘述結構。
畫科在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期變得更加完善。徽宗御製的《宣和畫譜》將231名畫家分入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十門之中。其他畫史著作如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和鄧椿的《畫繼》(均寫於12世紀),雖然使用了時代、造詣和身份等標準,但也都以畫科作為確定畫家專業的最基本因素。如《畫繼》把北宋熙寧七年(1074 年)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間的219名畫家置於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車、蔬果藥草和小景雜畫八門之內。畫科的出現和發展雖然一般被作為“藝術史學史”的題目,但實際上是繪畫話語和繪畫實踐的綜合產物,一方面標誌了藝術概念的突破,另一方面也為山水、花鳥、仕女等畫種的獨立發展提供了新的基礎。
進而考慮繪畫的社會性和贊助系統以及畫家的身份及工作環境,五代至南宋這一時期也見證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即中央朝廷和地方政權對繪畫創作越來越深的參與,以及由此導致的繪畫創作的行政化和機構化。宮廷任用職業畫家自然不是此時才出現的現象——以往各朝皇室已把精於醫藥、占卜、星相、書法、圖畫等技藝的人才攏入內廷為己服務。如唐代在掌管圖書的集賢殿書院下設有“畫直”,其職能從“修雜圖”逐漸擴大為“奉詔寫真”。但只是從10世紀開始,才出現了皇帝將相當數量的第一流畫家集聚在宮廷中的現象,其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導致了畫家的流動,二是對繪畫具有濃厚興趣的統治者對這門藝術大力扶持。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位於成都和金陵的兩個繪畫中心——二者分別是前後蜀(907—966年)和南唐(937—975年)的都城。宮廷繪畫在宋代被進一步制度化,先是出現了名為“翰林書畫院”的官方機構,徽宗(1100—1126年在位)繼而創立了“畫學”“書學”和“翰林圖畫院”,在全國範圍內吸納有才能的畫家。這位皇帝通過自己的直接參與,把宮廷中的繪畫創作結合以臨摹和藝術教育,形成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綜合性宮廷繪畫系統。南宋畫院的具體情況雖然在史籍中語焉不詳,但大量實物證據表明宮廷繪畫在這一時期中具有更強大的影響。如此時最著名的畫家幾乎都為朝廷作畫,其地位也較前代宮廷畫家有明顯提高,一些人被授予金帶甚至出任朝官。與兩宋制度呼應,北方的遼代在翰林院下設置了“翰林畫院”和“翰林畫待詔”,隨即的金代宮廷則建有畫家供職的“祗應司”。甚至在遙遠的西北,敦煌地區的歸義軍政權也設立了畫院機構。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考慮,可以看到
宮廷畫院是此時期的一個普遍現象,反映出繪畫的組織結構從寺廟和作坊等基層單位向高層行政機構的轉移。宮廷畫院的建立從表面上看是制度史的問題,但實際上與繪畫的內容和風格不可分割,因而構成中國繪畫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宮廷繪畫的最大特點,是其興盛取決於統治者的個人興趣和參與,其面貌與統治者的趣味和目的直接相關。但從另一方面看,帝王的趣味並不完全是個人性的,也受到當時政治形勢和文化潮流的影響。這一時期宮廷繪畫中的一系列現象——包括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鍾愛的“大山堂堂”圖式、徽宗畫院推崇的裝飾風格、高宗朝(1127—1162年)繪畫的強烈政治主題——都見證了這種影響。對宮廷繪畫的研究因此既需要考慮皇帝的喜好,也需要考慮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文化潮流,特別是宮廷繪畫和文人繪畫的互動。這種互動在這一時期裏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並由此發展成為中國繪畫史的一條核心線索。
雖然嚴格意義上的文人畫傳統是在這個時期之後形成的,但北宋至南宋的作品和畫論明確顯示出文人階層在繪畫實踐和話語兩個方面越來越強大的影響。此處所說的“實踐”包括對私人性繪畫媒材的注重、對表現個人思想感情的強調、對“詩書畫”關係的推崇,以及由此出現的特定繪畫題材和風格追求。“話語”則包括了文人有關繪畫的各種寫作,如畫論、題跋、詩詞、筆記各類,反映出他們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他們從往昔時代尋找符合自己趣味和價值觀的先驅者,因而開啟了撰寫文人畫史的先聲。這一潮流與宮廷繪畫的關係是個複雜而微妙的問題——雖然二者在概念層次上常被置於對立的位置,但在實際歷史發展中往往處於具體而微的互動之中。雖然帝王倡導下的宮廷繪畫決定了當時的主流風尚,但孕育中的文人繪畫也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其美學觀念影響了宮廷趣味和宗教繪畫的風格。文人畫的發生和發展因此不應被看作文人圈裏的封閉現象,它最終成為中國繪畫主流的一個基本原因實際在於它對其他領域的持續滲透。
從繪畫史的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看,這一時期也有著它的獨特性。最重要的是,我們首次掌握了一批傳承可徵的獨幅畫作,包括原件和早期臨本,有的並有可信的作者和贊助人。但從另一方面看,南宋以前具有明確畫家歸屬的畫作仍屬稀少,大部分傳世作品存在著時代、真偽和作者等問題,是書畫鑒定家長期爭辯的對象。有關畫家的信息 —包括當時的最著名的畫家——也仍然非常有限。雖然畫史記錄了這一時期中許多畫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作品名稱和風格傾向,但這些記載多為簡略的描述和品評,很少涉及畫家的人生經歷和藝術探索。這一情況使我們反思以往繪畫史寫作中的一個主要傾向,即美術史家以這些簡短的描述為根據對畫家進行高度概括,將其藝術創作濃縮為單一面貌,進而以此作為鑒定傳世作品的依據。但中外美術史都告訴我們,任何重要畫家的藝術生涯都必然是一個摸索和成長的過程,其繪畫題材和手法的變化是常見的現象。後世文獻對此期中國畫家的高度概括主要是歷史證據匱乏的結果,並不一定反映了藝術家的整體面貌。
出於這些原因,雖然以畫家為線索撰寫此期繪畫史是一個長期以來使用的方式,但實際上在文獻和實物兩方面都缺乏足夠的根據。繪畫史作者也往往陷入兩種困境,或不斷重複高度概括的傳統文獻,或對有限的傳世作品進行無休無止的論爭。針對這些問題,本書把歷史敘述的基礎從“畫家”轉移到“作品”上。所使用的作品包含兩類,一是真偽和時代不存問題的考古美術材料,包括墓葬中發掘出的畫作和遺址中現存的壁畫;二是大多數繪畫史家接受的傳世繪畫作品和一些來源有自的早期摹本。一些赫赫有名的畫作如果不屬於這兩個範疇的話,也就不作為關鍵歷史證據在此書中出現。總的說來,由於歷史材料的限制,本書的主要任務不是追尋重要畫家的思想發展和藝術軌跡,而是通過分析繪畫作品——包括許多無名畫作——綜合出此時期中國繪畫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