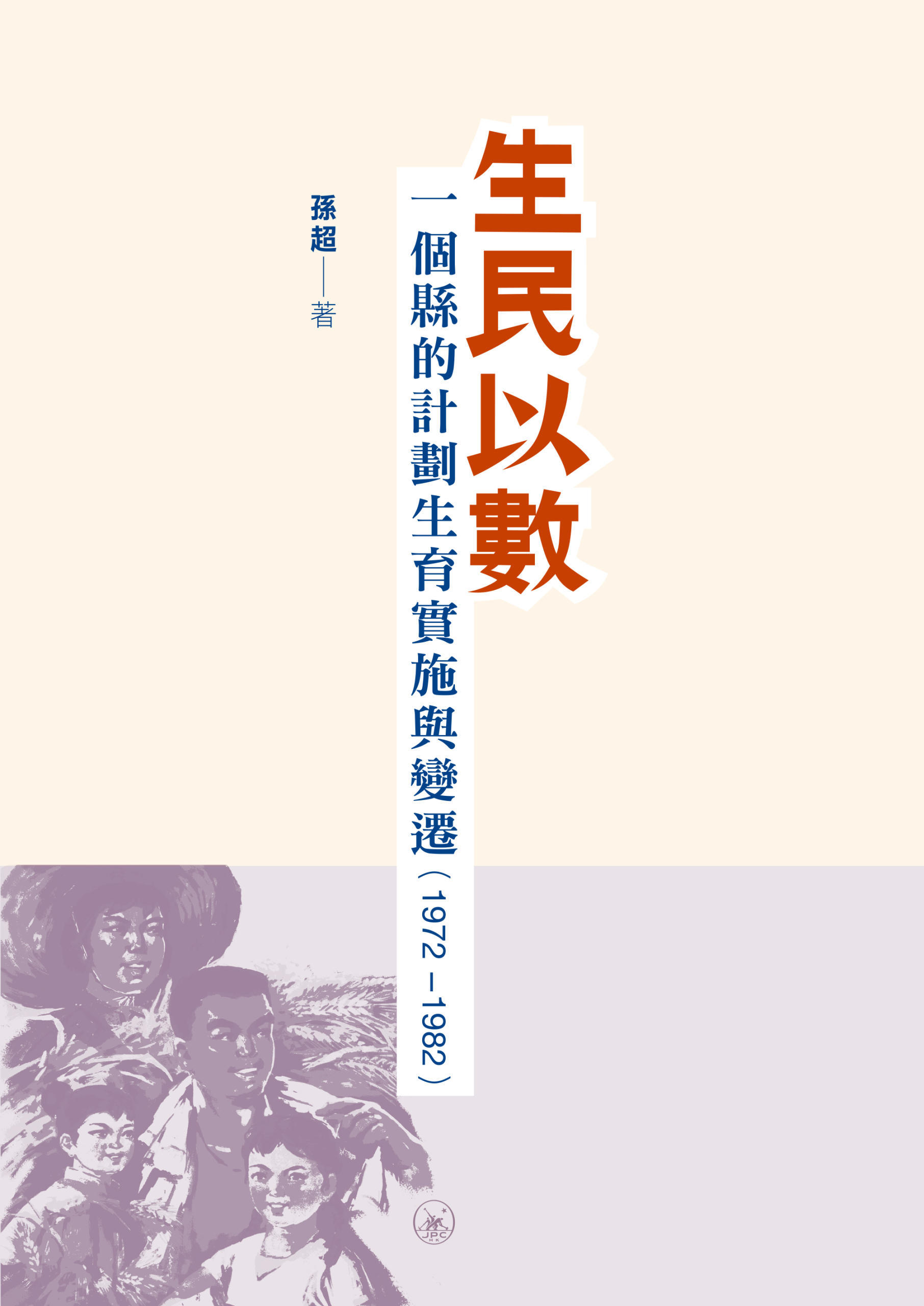生民以數:一個縣的計劃生育實施與變遷(1972-1982)
簡介
在這場橫跨半世紀、影響深遠的計劃生育運動中,社會發展如何與民眾際遇相互影響?制度設計如何在基層社會實現計生效果?地方執行者又如何在政策框架下尋求平衡?
本書選取西部甘東縣為研究案例,通過扎實的田野調查與珍貴的一手資料,重現1972至1982年間從“晚稀少”到“一胎化”的政策演變過程,探討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組織機制與地方適應策略。
這既是一部記錄人口政策變遷的實證研究,也是對現代國家治理方式的學理探討。在人口調控的實踐中,展現了政府、社會與個體之間的複雜互動。
目錄
圖表索引 13
第一章 研究背景 15
一、全球生育控制 / 17
二、中國計劃生育 / 23
三、基本問題與思路 / 2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9
一、國家體制的視角 / 32
二、權力技術與反抗 / 33
三、官僚組織研究 / 36
第三章 方法與對象 39
一、個案研究 / 42
二、資料收集 / 44
三、甘東縣情 / 49
四、計生機構 / 53
第四章 計劃生育的開展 59
一、背景環境 / 62
二、節育高潮 / 76
三、計生動員 / 95
第五章 “晚稀少”的困境 105
一、遺留問題 / 108
二、工作收緊 / 124
三、晚期引產 / 135
第六章 “一胎化”的出現 147
一、觀念變化 / 149
二、公社解體 / 161
三、政策實施 / 174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187
一、計生變遷的內在動力 / 190
二、“一胎化”與治理術 / 195
附錄一 主要訪談對象情況 203
附錄二 人口的政治:70 年代末嚴格計生政策出台原因探析 205
參考文獻 223
作者簡介
孫超
1986年生,法學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現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人口政策、發展問題、基層政府,曾在《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學術論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
序/導讀
自序
這本書修改自我的博士論文,大體是2015年確定選題方向,2016年調研收集資料,2017年正式開始寫作,2018年完成並通過答辯。雖然藉著出版的機會,我補充了一些新近文獻,但總的來說,本書(尤其是第一、二章)只能反映2017年前後學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進展,謹請讀者注意。
從論文選題到現在,差不多十年了。回頭看,這段時間恰好是中國的又一個生育劇變期。新增人口數、自然增長率都在2016年之後掉頭直下,短短數年,出生數直接腰斬,總人口更是前所未有地進入負增長。當然,在我寫作博士論文的那幾年,還看不清這種趨勢。當時大家仍沉浸在“全面二孩”帶來的生育反彈中,有人甚至主張回歸“一胎化”,認為隨著政策放鬆,人口又將失控。
過去幾年中國人口生育的快速變化,既令人感慨,也發人深省。我們對人口問題的理解恐怕還有很多局限,對人口規律的把握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深刻。今天的人口學,研究對象早已變成各種數據,分析方法也高度量化,看上去十分接近自然科學;但對於基礎性的人類生育行為和人口變化規律的認識,其實和馬爾薩斯時代並沒有根本區別,大體還是來自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歸納,而非基於堅實公理之上的邏輯演繹。
這一點和過去幾十年中國人口觀念、人口政策的“翻燒餅”有很大關係。50年代末,“人多力量大”壓倒了節育的主張;70年代末,社會精英集體轉向強調人的消耗性、主張嚴格控制人口;到了21世紀10年代,“人口紅利”大為盛行,人口又變成最可寶貴的資源了。幾乎一代人的時間,看法就會翻轉一次,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並不真的掌握影響人口生育的根本原因,總是用當時的現象去推論未來。時間一久,屢屢失算。同樣,今天大談的“低生育陷阱”也是基於過去幾十年一些國家的生育現象,導致這一點的原因是什麼,人類生育會被哪些因素改變,未來人口趨勢如何,其實並沒有十分確定的答案。
上述感受在我準備博士論文時就已經萌生。確定大概方向後,我開始粗讀文獻,主要是政策文件和一些二手研究。隨著閱讀增多,我越來越對70年代末計劃生育從原本寬鬆的“晚稀少”轉向極為嚴格的“一胎化”感到困惑:改革開放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國家權力在各個領域收縮、與民休息,但為何同一時期的計劃生育反倒變得更為嚴格?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促使我在2016年春嘗試寫作了“人口的政治:70年代末嚴格計生政策出台原因探析”一文。核心觀點是:人口政策嚴格化和改革開放寬鬆化一體兩面,都是為了應對“文革”後中國的落後現實。因為落後,所以必須改革開放;但對為何落後的追問又需要一個“阻斷機制”—建國後快速增長的人口恰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既然中國的落後主要不是總量少,而是人均水平低,那就說明問題不在國家體制,而在人口太多。計劃生育因此至關重要,走向嚴格的“一胎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計生嚴格化與70年代末中國的發展困境有關,這一點已經有學者提過,並不算新。我寫這篇論文的初衷是用更多歷史材料加以論證。文章寫成後曾投稿發表,但因篇幅過長,刊出時不得不刪去大半。藉著本書出版的機會,我將其作為“附錄”,全文收入。
現在看去,“人口的政治”中一些推論邏輯還不夠嚴密,除了自身學術水平的限制,這也和材料來源有關—一旦涉及高層決策,公開資料不多,光靠文件和講話,難以窺見全貌、釐清過程。因此寫完文章的我更堅定了通過調研收集材料的想法。之後不久就前往甘東,在那裏待了半年。調研經過書中有介紹,不再贅述。總之,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得以完成博士論文,要歸功於當地朋友的幫助。不過出於現實考慮,也是尊重他們的意願,不再一一致謝了。
過去幾年生育變化的另一個後果是,在人口問題不斷引人關注、變成熱點的同時,關於歷史上的人口政策、尤其是計劃生育的研究迅速萎縮。這部分是因為政策重點轉向鼓勵生育,嚴格計劃生育成了過去式,學者的興趣有所下降。但從2013年生育政策調整後反倒出現一個研究高潮來看,興趣問題未必是主要原因。更可能的是,隨著生育率“雪崩”,人口形勢陡然嚴峻,曾經的生育政策和計生歷史在現實中變得微妙起來,學術期刊也多傾向於不發表。
這種情況下,本書能夠出版,十分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尤其是出版經理李斌先生和責任編輯王逸菲。在此之前,我以為本書要想面世不容易。沒想到年初,偶然聯繫上了香港三聯書店,李斌先生看過文稿後即惠允促成,並在隨後高效推動相關事宜。本書改自博士論文,內容蕪雜、徵引繁複、圖表頗多,又涉及內地與香港兩地的體例格式、表述習慣差異,很多地方都需修改調整,責任編輯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對兩位的付出深表謝意。
當然,上述歸因掩蓋了一個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成為過去,對其歷史的研究還有什麼學術價值,又是否值得出版?我的看法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發端、70年代全面推開的計劃生育,綿延半個世紀,波及十多億人,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這為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提供了難得的案例,計生史研究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人口不管如何變化,都擺脫不了既定的歷史。現實問題越突出,越需要回答曾經發生了什麼、何以至此。本書提供了一種對這段歷史的解釋,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正確的,但可以和其他研究一起,豐富對過去的理解,揭示其中的複雜性,盡量避免過分簡化歷史以致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此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保留一點史料。計生初興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隨著時間拉長,親歷者也在逐漸凋零。很多與之相關的故事和道理如果不去詢問記錄,將永遠消失。本書不光使用檔案文件,也對當事人做了一些訪談,算是為早期計生史提供了一點新的資料,這對以後的研究或許會有幫助。倘能如此,出版也就有意義了。
按寫作論文時的設想,我將在畢業後幾年對甘東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計生史做整體研究。博士論文如果等到那時再修改,應該會完善很多。不過世事變化,研究最終還是止步於1972—1982年,後續計劃已無法實現。關於過去半個世紀的計劃生育,我還有些書中未及討論的想法,藉此略陳一二,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計劃生育的獨特之處在於長期性、普遍性和徹底性。作為一項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相當大的範圍內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這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歷史中並不多見,即使農業稅也未必能與之相比。這些特點使得計生實施包含了大量有待研究的問題。
比如,政策指標與民眾意願的衝突。70年代末以降,政策生育數長期低於民眾的理想生育數。推行計生的正當性快速衰減,實施成本愈發高昂。這既構成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可採用的組織方式和技術手段。值得思考的是,政府為何要推行一個最初並不被民眾廣泛接受的政策,又如何將其落實下去?可以說,這個問題是貫穿本書的主線。
再如,嚴格執行與普遍變通的並存。由於和民眾意願相左,落實計生的一種可能選項是強力推行。這在大量海外研究和個別案例的印證下,塑造了計劃生育不那麼受歡迎的基本形象。但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又表明,計劃生育在現實中似乎遭遇了普遍且有效的應對,執行時的變通大量存在。那麼,一個廣泛變通的政策又何以談得上被嚴格執行?
又如,複雜內容與變動環境的協調。計生政策包含了“晚稀少”“嚴格一胎”“一孩半”“雙獨二孩”等不同內容,在推行計生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從計劃體制走向雙軌制、市場經濟、全球化。伴隨農村公社制和城市單位制的鬆解,基層社會的組織治理方式也處於不斷轉變之中;更不用說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漢族為主區域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巨大差異。在一個政策內容和社會環境都變化多樣的時代,計劃生育目標是如何實現的?
以上種種,令人困惑,對其的思考也貫穿了我從田野調查到論文寫作、再到後續研究的整個過程。在我看來,要回答這些疑問,必須從歷史入手。計劃生育雖然延續幾十年,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鮮明的階段性特徵。一些問題看似弔詭,其實只是因為把不同階段的特點放在了一起。
基於對甘東的研究,我將70年代以降的計生工作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2—1982年,也就是本書論述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晚稀少”政策為主,依靠強有力、全覆蓋的公社和單位制,全面動員,普遍實施。1980年前後,轉向“一胎化”的人口政策與民眾意願大為背離,實施難度陡增;與此同時,隨著農村改革普遍推行,公社體制瓦解,國家對生產生活物資的控制力和分配權明顯削弱,原本的“運動模式”難以維繫。
以1983年開始的“大結紮運動”為標誌,甘東計生走向“突擊模式”。這種模式不再追求全面無死角的政策落實,而是“軟處取土,硬處打牆”,依靠周期性的計生運動和年內兩次突擊行動,集中力量,由難入手,整村清茬,帶動其他。從某種角度講,這一時期的計生實施可以視為第一階段“運動模式”的弱化版。
前兩階段的共同點在於計生工作的關鍵都是如何將政策落實下去,只是因為政策內容與可用資源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到1995年前後,甘東計生工作進入新階段,我稱之為“迎檢模式”。在這個階段,核心問題發生變化,從“如何落實上級政策”變成“如何讓上級相信政策落實了”。基層計生部門將大量人力、精力投入到圍繞上級檢查的攻防戰中,各種應對檢查的技巧手段層出不窮,計劃生育的“迎檢遊戲”(艾雲,2011)也由此而來。
從計生實施的角度看,90年代中期實為一個重要分水嶺,其意義不亞於70年代末的“一胎化”轉變。這也反映在歷年節育手術變化上。
從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各類節育手術大體四五年一個循環,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波動。這源於前兩個階段計生實施的特點,即當任務緊迫、現實阻力較大時,往往在全國範圍內發起計生運動,形成節育高潮;但這些運動又無法持續,於是高潮之後是相對的低谷,隨著時間推移,問題不斷累積,又呼喚出一場新的運動。
但進入90年代後期,原本鋸齒般變化的節育手術量趨於平滑穩定,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的是周期性計生運動的終結。當然,不是說此後沒有計生運動,而是說此後的運動對現實生育行為的影響已經相當有限了。這和歐美學者所說的中國計劃生育的“新自由主義轉向”(Greenhalgh & Winckler,2005)大體是同一個過程。
那麼,計生工作為什麼會在90年代中期發生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我也沒有充分的把握,只能粗略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這與90年代後期人口政策轉變有一定關係。到1998年前後,世紀末人口保持在12億左右的歷史任務已基本宣告實現,人口控制壓力陡然減輕。此後國家層面也沒有再提出具體的人口目標,計劃生育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下降。
不過這也並非全部原因。以甘東為例,在1996年前後的計生運動中,“迎檢模式”就已經有所體現了。導致轉變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整體變遷,具體地說,就是90年代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新體制之下,城鄉藩籬逐漸打破、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速、人口流動更加頻繁,這些帶來了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生育觀念的變化。到90年代中後期,“超生游擊隊”的形象事實上已經過時,民眾生育水平普遍下降,推行嚴格計生運動的必要性大大減弱。另一方面,90年代一系列改革(如分稅制,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使行政體系內部的工作方式、風氣氛圍都發生變化,計生工作模式也隨之轉變。
“迎檢模式”持續了十年左右,到00年代中期,計生工作又出現新的特點,走向“報表模式”。新變化的背景是進入21世紀,農村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本地計生對象迅速減少,而且由於人口頻繁流動,計生部門也很難掌握實際情況。結果就是考核檢查日益例行化,時間、內容、形式高度固定。上級不再試圖通過突然襲擊或抓住各種蛛絲馬跡去推測詰問真實狀況,下級也不再花大力氣打探消息、提前佈局、臨場發揮。考核時雙方都像按既定劇本表演,整個過程規範且平淡。
在這一階段,基層計生工作的一個重點是跑項目。隨著中央財政改善,計生部門經費在00年代迅速增長,轉移支付力度隨之增大。這些經費大都通過項目方式下達,因此對基層而言,如何向上爭取各種專項(如二女戶補助)、獲評各類稱號(如創省優、創國優)變得重要起來。
相應地,基層的日常工作變成填寫各類報表。到0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傳統手工報表徹底被網絡數據庫(如WIS、PADIS等)替代。相比而言,數據庫的管理權限上移,上報後難以修改,對數據邏輯關係的審核也更嚴密。於是,大量基層計生工作者也被“困在系統裏”,用他們的話說,“不在工作上下功夫,專在數字上做文章”。要編的報表越來越多,下鄉入戶越來越少,整體數據也愈發失真。
到00年代中後期,計劃生育主要成了紙面工作,或是基層“放水養魚”的幌子,對實際生育行為的干預已經很少了。也許正因如此,2012年陝西的計生事件才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這並非大家對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忍無可忍後的最終爆發,而是震驚於一個近乎銷聲匿跡的“怪物”居然會突然復活。
不過到這時,以控制人口為主旨的計劃生育已經走到盡頭。2013年,中央開始調整生育政策,逐步放開二孩;同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被整合進新成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作為單設部門。到2018年,中國的新生人口開始暴跌,“計劃生育”四個字也從國家機構名中徹底消失。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計生時代”終於徹底落幕。
只是對計劃生育而言,蓋棺並不意味有了定論;恰恰相反,關於其中很多問題、乃至整體歷史評判的爭論才剛剛開始。本書若能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或是引起讀者對這個議題的些許興趣,便算得上成功了。
最後,我從本科到博士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接受教育,社會學的知識和“想像力”至今讓我有仰高鑽堅之歎。本書能夠完成,應歸功於學界前輩的薰陶和系裏老師的教誨,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劉愛玉教授,她給了我充分的選題自由,在我猶豫不定時又大力鼓勵,並指導了論文寫過的全過程。朱曉陽、張靜、周飛舟、渠敬東、謝桂華、佟新、應星等老師對論文寫作給予了很大幫助,他們在授課和討論中閃爍的洞見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學術水平。
從論文到成書,雖然幾經修改,疏漏之處仍如地上落葉,旋除旋生。不辭固陋,率爾付梓,先著一鞭,以為引玉。懇請讀者包涵指正。
2024年7月8日
於北大燕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