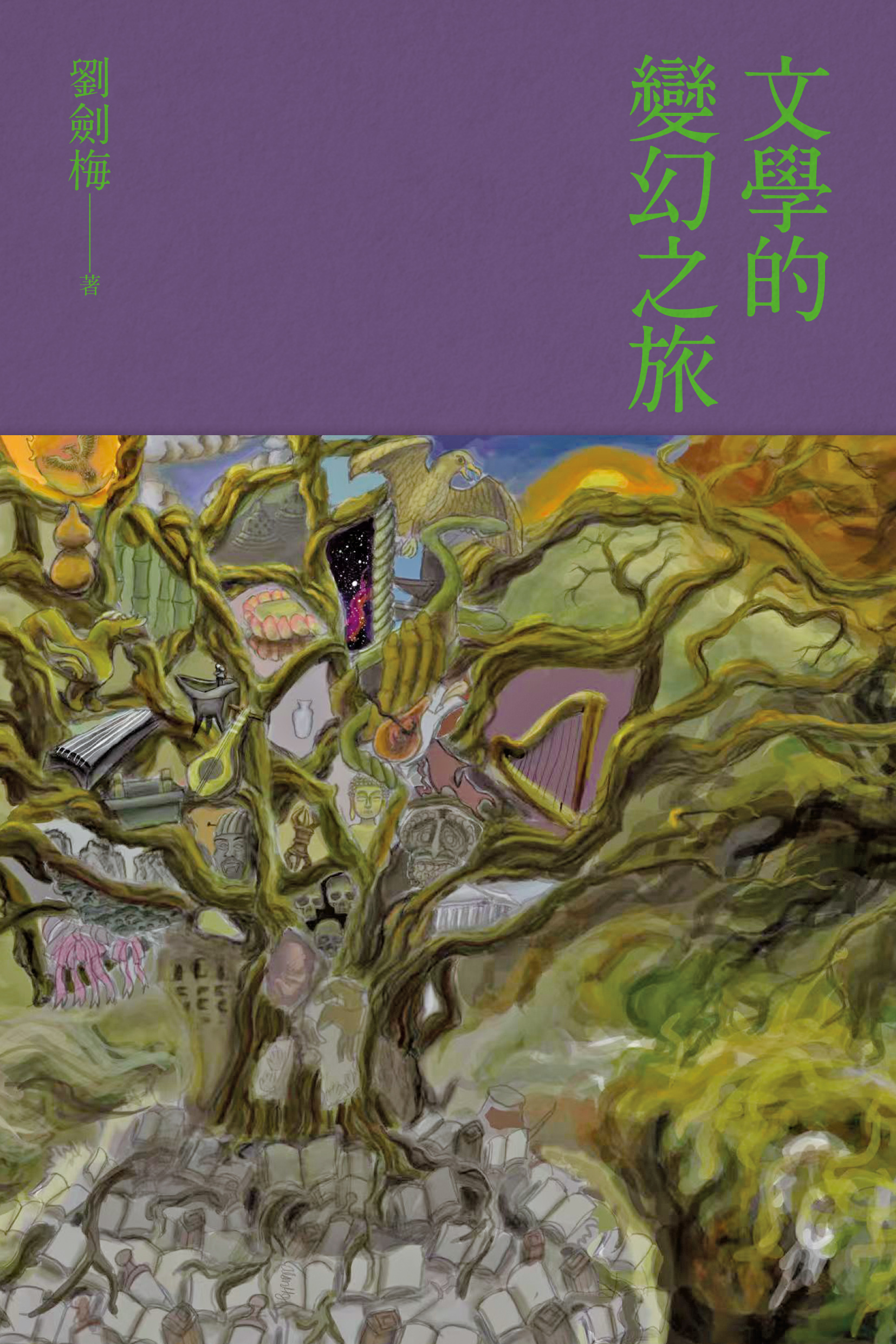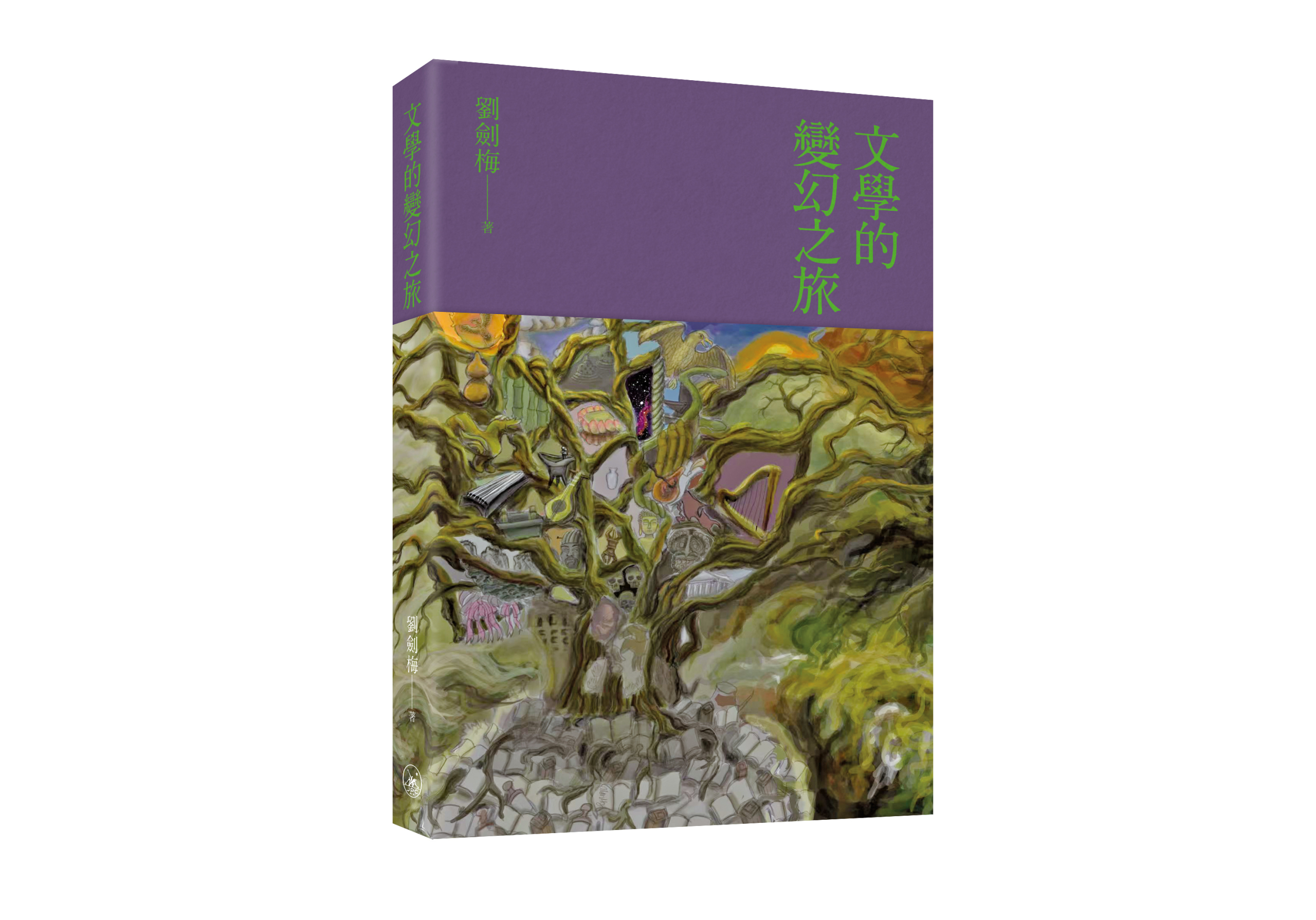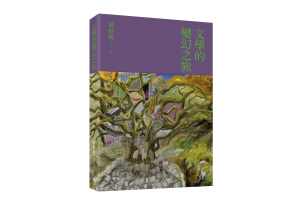文學的變幻之旅
簡介
這是劉劍梅教授近年在香港科大寫作的閲讀筆記,她稱之為是“對文學的一次真正的回歸”。其靈動的文筆與嚴謹的學風,帶給人極大的智性愉悅和啓悟。
跟現實生活相比,文學具有雙重性——既是現實生活的記錄,又常常超越現實生活。在寫作中,作家的思想有如莊子的鯤鵬一樣,可以完全自由地思考和飛翔,無邊無界。此書探討的女性作家大膽地跨越了男權社會規定的“家”的邊界;談到博爾赫斯的夢、舒爾茨的濃彩一般的幻想和“變形”主題的演變如何跨越各種疆域;還討論文學的各種維度,包括現實維度、歷史維度、宗教維度和思想維度。
這裏談及的女作家有美國的瑪麗蓮·羅賓遜、印度的阿蘭達蒂·洛伊、韓國的韓江以及波蘭的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作家作品還有波拉尼奧的《2666》、薩曼·魯西迪《午夜之子》、格雷厄姆·格林的《權力與榮耀》、遠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庫切的《伊麗莎白·科思特洛:八堂課》、托馬斯·曼的《魔山》、法國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 馬爾克斯對疾病的書寫、索爾·貝婁的一系列小說等。
目錄
序一 被現代情懷滋養的經典析說 閻連科 / i
序二 作為魯迅之後一百年的小說小讀者 駱以軍 / xiii
第一輯 女性的水上書寫 / 001
家—女性的憂傷 / 003
靈動婉轉的散文體小說 / 029
第二輯 文學的變幻之旅 / 055
博爾赫斯的夢 / 057
色彩繽紛的舒爾茨 / 082
“變形”的文學變奏曲 / 105
第三輯 文學的各種維度 / 139
文學如何面對暴力 / 141
互綁的個人與歷史 / 169
關於靈魂的書寫 / 194
思想—小說的另一條路 / 216
心靈的孤本 / 243
第四輯 文學隨筆 / 261
拒絕遺忘的書寫 / 263
關於書的輓歌 / 271
書寫疾病和歷史 / 281
後記 / 295
作者簡介
劉劍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席教授。英文專著包括《中國第三空間:中和政治的悖論(1946-2020)》、《莊子與中國現代文學》、《革命與情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中文著作包括《小說的越界》、《徬徨的娜拉》、《狂歡的女神》、《共悟人間》(與劉再復合著)等。
名人推薦
劉劍梅是上帝經常去看望的那個人。因為上帝讓她出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和特殊的家庭,父親的博學與慈愛,以世為家的寬廣和超越,加之特殊的命運安排她西去留學與求讀,苦難恰恰成為她閱讀的方舟和擺渡。《文學的變幻之旅》為這個文學時代的上空,清晰劃過一道“越界”的光,為今天的讀者、作家和論家,留下了超越中文的更為寬廣、獨特、自由的論說和飛翔的身影。
——閻連科
推薦序
被現代情懷滋養的經典析說
閻連科
理論與小說寫作的隔膜,一如北方的老榆和一棵南方棚大的榕樹,幾無可談的相似之處,使得我們經常在左耳聽到作家信誓旦旦地說,我從來不讀文學理論書;又幾乎是同時,在右耳聽到理論家面帶譏笑道,當代文學實在難有可讀之小說。這種兩相對立、互不心往的狀況,不僅宛若北方的榆樹和南方之榕樹,怕也是同一片土地上的菊花和野草、野槐與荊棵,你開你花,我生我葉,並無實質之交錯,只是在外人眼裏,榆樹和榕樹都是世間的一場樹木吧。野草、菊花、荊棵和野槐,都是人世的綠中之植吧。源於這樣久常的疏離和隔膜,每每使人讀一篇或一本能夠如渴之飲的文本批評或理論,便會覺得比讀了十本、二十本每天都在出版、每日都在書店的貨架上擺上或撤下的小說要勝好著許多或太多。
作家等待和尋找如渴之飲的文學批評,如同批評家朝日求找一部可讀可言、言而不煩的小說。此間兩相的抱怨和根恨,在雙方的胸腔之深處,已經懟埋了太久、太深遠,只是中國的文化和人情,讓彼此笑而不談並彼此心知肚明地飾而不言著。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冷笑、隔膜和彼此難有正眼相視的奇情與異狀,讀到劉劍梅教授這一系列對現代經典的析閱論說時,先是感到有一種消除隔膜的親近感,後是那種兩相根恨如柏林牆樣被推翻的豁然和開朗。及至她將這一系列的文章彙編為《文學的變幻之旅》後,再一次地集中之閱讀,便突然有了那種“等到了”、“找到了”的喜悅和興奮。
實實在在說,很久沒有讀到過對自己和諸多讀者都共同心儀的作家和作品有個人見地或共識相似的理論著作了。《文學的變幻之旅》,是一個批評家的私人閱讀史,也是這個批評家與作家和讀者的共同閱讀史。而這其中談到的偉大作家和作品,是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幾乎都讀、卻又少有成文的理論去梳理和言說。《文學的變幻之旅》就在這時如期而至了。它既不東拉西扯地去賣弄和裝點,也不仰視、膜拜地將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當做耶穌和《聖經》,擺在文學的聖桌上供奉和恭敬。每一篇的閱讀和剖析,只是要告訴你“我喜歡和我為什麼會喜歡”。親近、隨和,並發自內心去分享,而非因為“我要理論”才去說,才去讀,才去引經據典地寫出來。原來在文學理論中,“我喜歡”和“我要寫”,是這麼不同的兩件事。前者因為喜歡才去讀和寫;後者因為要寫才去讀。當二者都成為理論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時,前者的文字、文章中,呈出一種自然親切的欣悅感,後者呈出一種肅嚴、正經的呆板感。前者的輕鬆、欣喜一如坐在茶館、咖啡館的相遇和聊天,無非彼此見面聊的不是吃飯、穿衣和住房,而是我最近讀了什麼書,為什麼會喜歡這些書;而後者,則如教室中的老師和學生、講台與課桌樣的距離及隔閡。因為後者一上來,老師就對學生說,現在上課了,請大家都拿出筆和本。
再次讀完《文學的變幻之旅》而收合尾章時,我沉落在這本給我帶來喜悅的理論書冊裏,於是想到這喜悅的源淵出處了—十二篇的文章,談到了百來作家和上百部的書,並不是每個作家和每本書都使我喜愛並欣悅,那麼為什麼一本理論著作的文章和通篇之析作,又篇篇會讓人感到不間斷的喜悅和親近?如同閱讀一部你並不完全喜歡、卻又讓你一字不落地去品味的作品樣。如波拉尼奧的《2666》這巨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讀完了它?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喜愛它?到底那些喜愛它的作家和讀者,有幾個能說出因之喜愛的一二三?大凡一站到人前就談論波拉尼奧和《2666》的人,我常用驚異的目光看著他們的臉,試圖從那臉上讀到一層人云亦云的盲從和虛偽。然在讀劉劍梅的〈文學如何面對暴力〉這篇對《2666》抽絲剝繭的作品分析時,她和她的文章讓我那種懷疑的目光變得溫和了、釋然了,隨性並也包容了。直到今天說,我都以為《2666》因為作家寫作前是為了五部小說而起筆,並非為了一部巨製的一次面世與出版,所以間,當將五部組合為一部時,結構上是有著明顯隔離和生澀的(當然也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游離而又聯繫的新結構),然由於我們對波拉尼奧的寫作與離世,深懷著敬重而不去挑剔這一些,所以在幾乎所有人都盲目盛讚《2666》時,我總是盯著那盛讚者的臉和眼—也就這時候,恰到好處地讀到了劉劍梅的〈文學如何面對暴力〉這來去有據的文本分析了,也是這時我對劉劍梅教授開始懷有了頓為愕然的敬重感。這種敬重不僅是她率先打破了《2666》的偉大連續多年都凝結停留在中文讀者和作家嘴邊的喧鬧上,以一個女性的獨有之目光,寫出了《2666》對世界、暴力和女人與人的強力、強大的關注和投入,而更在於在〈文學如何面對暴力〉這篇論文中,使人感受到了批評家的文學情懷是何等重要和關鍵。一如一個作家沒有情懷空寫出的小說樣,倘若一個批評家,沒有情懷而去析說理論時,哪怕你的才華、聰智大如山脈與海洋,寫出來的文章、著作怕也是沒有血脈的積木建築吧。
我想應該是這樣—當我們說沒有情懷的小說就是沒有靈魂的篇章文字時,也是可以說,沒有情懷的理論,同樣是沒有靈魂的篇章文字著。從面對波拉尼奧到面對舒爾茨,從面對舒爾茨到面對托卡爾丘克,再到她面對奧維德和他的《變形記》,這一路的讀來和析說,在劉劍梅的文本分析與縱論橫比中,我們始終在她的理論述說裏,可以真切、清晰地讀到她對人與人世的愛,讀到她對文學天然的情感與糾纏,對語言創造發自內心的敬重和對孤獨寫作者無條件的擁抱和同暖。一如她在〈文學如何面對暴力〉中說的樣:
波拉尼奧對全人類範圍暴力的書寫,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們內心冰海的冰鎬。它不僅質疑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及精神出路的問題,而且通過小說的形式繼續探討斯坦納提出的大哉問。那就是面對人性的野蠻和邪惡,文學和語言是否已經失去了其本來應該具有的人文精神,還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現和批評現實中的暴力和謊言,發出吶喊,讓麻木的人們為之震顫?那些知識的承載者,是否已經全軍覆沒,對黑暗的世界無能為力?
這樣一段深具現代意義的盤詰叩問的胸腔文字,劉劍梅說的是《2666》,但也同時是她詰問著整個的世界和文學。是她面對文學的一種現代情懷,也是一位女性面對自己的閱讀和寫作的現代情愫。而整個一部《文學的變幻之旅》,也正是她“面對人性的野蠻和邪惡,文學和語言是否已經失去了其本來應該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分析與對答。
正是在這個最基本的現代情懷基調上,劉劍梅和她的〈文學如何面對暴力〉,讓我們理解了波拉尼奧和他的《2666》,也讓我們深明了《文學的變幻之旅》這部批評家、作家和讀者所共有的閱讀史和經典文本分析史。於是間,我們看到了一個批評家建立在對文學灼情摯愛基礎上的寬廣和無際。在時間的線軸上,她根繫中國古典的老子、莊子、百家和西方文明的古希臘,一篇〈“變形”的文學變奏曲〉,宛若一碗水中盛裝了大海、山脈和世界,從希臘神話到古羅馬,從奧維德的《變形記》,再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和舒爾茨的《肉桂色的舖子》、《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從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到果戈里的《鼻子》、埃梅的《穿牆越壁》及至20世紀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魯西迪的《撒旦詩篇》和《摩爾人的最後嘆息》,及當今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的《乳房》,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牆》、《砂女》和《箱男》,法國作家達里厄.塞爾的《母豬女郎》等,然後是中國古典《莊子》中的“莊周夢蝶”,《山海經》和《聊齋志異》及至當下中國作家賈平凹、莫言、余華、遲子建等人作品中的鬼神變化和怪誕,一線珠串,灑灑洋洋,通過“變形”這一文學的意象、方法和鏡照,在時間上自古至今,在空間裏由西到東,拿來時如開箱取物,放下時如閉門離去,信手拈來,自由自然。這不由得不使人感嘆寫作者的閱讀和記憶,在這“變形”的一繩珠串的牽引下,使得文章中的每一書、每一例、每一故事和章取,都貼切到如落葉在秋,晨珠黎明,恰到好處地拿來,又恰到好處地放下。還有這冊批評集中的〈靈動婉轉的散文體小說〉、〈關於書的輓歌〉、〈思想—小說的另一條路〉、〈關於靈魂的寫作〉等,但凡有“縱論”性質的書寫,批評家都可上古下今、左西右東地論述和分析,其閱讀之寬廣,論說之自由,使人驚異和愕然。驚異她的閱讀量之大,愕然她的記憶力之好。而且在這如同“隨筆”樣的隨性論述中,她又總能以綱帶網地始終不離其主軸和主道,讓人隨步她的言說和分析,遍翻書頁,覽盡閱讀,一如一個圖書館的館長領帶讀者到圖書海洋的某一區域或某一架櫃前的尋找和檢索,直到你終於找到你要找的那本書,找到打開某一書架櫃門的那把鑰匙止。
以不甚恰當的方式說,面對20世紀的現代文學,我以為世界上最好的讀者,是那些可以拆解小說的人,一如最好的鎖匠,是那些可以配鑰匙的人。這群鎖匠就是批評家和會拆解小說的一些作家們。批評家的寬廣,奠定著他們的視野和深度;作家的寬廣,奠定著他寫作的坐標和方位。沒有閱讀量的批評家是不可思議的。沒有閱讀量的作家持續寫作也是不可思議的。從這個角度上說,劉劍梅是上帝經常去看望的那個人。因為上帝讓她出生在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和特殊的家庭裏,父親的博學與慈愛,以世為家的寬廣和超越,所有的人都是人的博大與情懷,這些來自父親天然的言傳和身教,如同家庭接力棒般的交接與續跑,加之特殊年代的命運安排她西去的留學與求讀,苦難恰恰成為了她閱讀的方舟和擺渡,當歷史更迭,朝夕時移,回望歲月給她的艱辛和酸楚時,又哪裏不是命運所賜給她的大天下的寬廣和幸運,哪裏不是成就情懷與胸襟之愛的神諭和安排。
當然著,並不是說人有了情懷和寬廣,成功與成就,便可以春種秋收般在時間和季節裏等著你的到來和收穫。對於好的文學和批評,世界上沒有無天賦的寫作和創造,也沒有單一地從閱讀中就可以孕生、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在於劉劍梅,在於這位充滿著對人和文學現代情懷的批評家,她對文學的敏銳,一如一個作家對故事和細節的敏感樣,如一個農人對天氣和未來季節變化的敏感樣。有人能從別人的一句閒談中觸摸到一部不同凡響的長篇小說來,有人卻只能從巨大的歷史動盪中提煉出一聲嘆息來。這也就是所謂的兌現天賦要透過敏銳的呈現與表達。換言之,文學的天賦或天才,相當程度上就是文學的敏銳性和敏感度。在托卡爾丘克於中文世界還相當冷寒的二年前,《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和《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在中國出版後,宛若一場倒春的寒流對新生楊柳的捲襲和閱讀凍冷時,劍梅總是和我談起托卡爾丘克的寫作與超越,並將她最早從英文讀到的《航班》的感受如餵食一樣告訴我。而當我的遲鈍門板樣還橫在她的敏銳面前時,關於托卡爾丘克文本分析的論文她已經寫將出來了。
我喜歡托卡爾丘克的散文體小說,因為這種文體輕盈、靈動、疏離,如同加了會飛起來的翅膀,帶我們飛越各種固定的沉重的邊界,飛離各種重複單調的表述形式,像淘氣的孩子一樣總是偏離軌道,在俏皮地逃離主流話語和傳統書寫方式的旅途中找到一種快感,一種釋放,在虛無裏看到生命,在生命裏看到虛無。
從她的〈靈動婉轉的散文體小說〉中,讀到她對托卡爾丘克寫作的這段精準論述時,我吃驚地在房間裏默站著。這種默然的站立,一方面是為那時自己對托卡爾丘克寫作的無知而驚訝;另一面,是對她敏銳的閱讀、感悟而愕然。儘管我自己並不完全認為托卡爾丘克的寫作是一種散文體小說,也不認為她一定就是碎片化的寫作,而覺得她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已有故事有意的重組和再塑,甚至覺到了她在這種重組、再塑中的艱難和鍥而不捨的嘆息與努力,但當批評家敏銳地意識到托卡爾丘克是“帶我們飛越各種固定的沉重的邊界,飛離各種重複單調的表述形式”的意義時,她那種對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把握和敏銳,又一次橫亘直立在了我面前。她總是能從中國文學最頑固、板結、封閉的土地上,敏銳到世界文學中最為鮮活的探索和衝擊,並能從中文以外的寫作中閱讀、回望、醫證出中國作家寫作在面對世界文學不可逆的潮進間原地踏步的腳音和無奈退倒的歌唱聲。正是因為這一些—從中國文學中走出去,又從世界文學中走回來,這種往復來去的每一次環行、觀望、醫證和比較,使得她的這些對現代經典的拆解、條理和析文,都懷著一種對世界文學的敏銳和對中國文學固封的焦慮在裏邊。也正是她反覆地從這塊土地、故文的出發和再回,使她率先去理析了《2666》對中國文學真正的價值在哪兒;托卡爾丘克的寫作,對中國文學寫作的意義在何方。乃至於面對沒有那麼知名的法國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小說《永恆的孩子》和《然而》,她也敏銳地寫出來了〈拒絕遺忘的書寫〉;面對舒爾茨的《肉桂色的舖子》和《掛有沙漏招牌的療養院》,這些作家們癡愛而讀者寥冷的小說,她又寫出了〈色彩繽紛的舒爾茨〉。還有面對魯西迪那難啃的骨頭《午夜之子》等,她都能直繫綱領地拆解和論述。〈互綁的個人與歷史〉,將《午夜之子》這棟複雜的建築拆解還原為原材料;〈文學如何面對暴力〉,將《2666》還原為一棟建築的骨架和地基;〈靈動婉轉的散文體小說〉,將托卡爾丘克小說中始終氤氳瀰漫的韵雲與氣息、時間與歷史,化解為雲、雨和日出,這種拆解和還原力,對於批評家正是敏銳和天賦,一如天才的作家總能把一滴水衍生為大海。且她的這種能力又總是和中國文學聯繫在一起—但凡在世界文學的書寫裏,有小說對中國文學有彌缺補憾之意義,她都能從缺憾的文學中走出去,透過敏銳的閱讀和感悟,到更廣闊的文學林裏徜徉後,帶著敏銳分析、比較的一橋一樑走回來。這些從文本出發的比較與論說,一面是為了改變中國作家的寫作而寫作;而另外一方面,乃至於她更多是為了“我看到”和“說出來”的自由而著筆。因此間,敏銳地發現,就成了她閱讀和論述的起點乃至為一個終點了,宛若一個敏於自己身有術疤的人,僅僅是為了對天氣的感應而持續存在著。
情懷、寬廣、敏銳—對《文學的變幻之旅》這本如此蘊含文學前沿意義的論文集,不能不說的是批評家最具個人意味的現代性。她的現代性不是我們日常說的小說寫作的現代性,而是一個批評家對20世紀文學現代性始終如一的傾情與關注,是批評家以一個女性或女性主義的獨有目光對文學的投射、分析和研討。這在中國諸多批評家中是相當鶴立雞群或獨一無二的,尤其以女性和女性主義的目光去瞻望或析說—這裏說的並不單純是指那篇她在這本書中對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優美論述:〈家—女性的憂傷〉—如同散文樣,娓娓道來地對美國女作家瑪麗蓮.羅賓遜的《管家》、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的《微物之神》和韓國女作家韓江的《素食主義者》的條理和分析,使得“家”這個如此煙火、世俗和溫暖的房居,被女性、現代的目光戳穿而成為女人籠窩的批評和批判;還有她在這本書中關注的所有作家和作品,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立場到格雷厄姆.格林和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當中文批評家多都對此沉默而三緘其言時,她卻是始終並反覆地提及和討論,始終將宗教、信仰作為現代文明和當下文學更應該關注的現代性的問題去讀、去說、去論述,如同她從來都不擱置、疏遠暴力、女性和女性主義的文學樣。還有文學中的時間、夢幻、結構、第三空間和現代生活與文學的碎片化等等,這些在20世紀文學中萬花筒般被反覆旋轉、變幻到使人眼花繚亂,而不得不使許多寫作者乃至整個中國文學都返回傳統和現實主義以喘息、歇棲、逃離和守成的寫作與閱讀,而她卻從來都以一個女性溫潤而執著的姿態,始終如一地相信時代無論如何是要向前的,文學可以回歸,但最終還是要向前的。她以這種理解退守、卻又稱頌執著前行的現代性,幾乎目不轉睛地盯在那些更有現代創造意義的作家和作品上。在《文學的變幻之旅》裏,她視博爾赫斯的夢和夢中夢,圖書館和圖書館中的書,迷宮和迷宮中的路,時間和時間中的空間及空間中的新時間“為文學加了起飛的翅膀”。因為“只有在夢中,作家才有虛構時間的能力,打破直線式的時間觀”(〈博爾赫斯的夢〉)。在〈五彩繽紛的舒爾茨〉中,她不光精密、究細地去論述舒爾茨小說中的變形、時間和夢幻,還獨有洞見地發現舒爾茨小說中的“自然精神”,看到了舒爾茨在他不多卻在小說中無處不在的“物質的深處,隱藏著無限的可能性。所有的物質—植物、動物、家具、窗戶、大門、牆壁、季節和我們生活周圍的點點滴滴的物質和環境,全部都等待著他來賦予其生命和靈魂。”這種對舒爾茨“自然精神”的洞明,除了閱讀與寫作的敏感,則更需要的是對小說現代性的高度認知。沒有這種更具現代意義的個人認知,我們則從根本和根底裏無法理解舒爾茨。〈思想—小說的另一條路〉,她從索爾.貝婁和他的《赫索格》、《晃來晃去的人》、《洪堡的禮物》等小說中以“思考”對人物、故事和風格的取代說開去,並以此延宕開來,討論一種獨有寫作的“迴心”、“向內轉”、“內心世界”、“內在經驗”及托馬斯.曼的《魔山》,庫切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但其被批評家要最終闡明的,卻是文學要擺脫“單一模式”的重要性和現代性。
我們當然不能說劉劍梅是現代小說的鐵定擁戴者,但在《文學的變幻之旅》一書裏,她讓我們通常被人道固有擁抱的人文情懷,幾乎毫無保留地轉移至了對文學、尤其是更具獨創意義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擁抱和頌揚上。她以一個女性批評家的獨立、洞見、綢柔、溫潤的筆墨,隨情隨性、自由無束地去討論幾乎所有在傳統的目光下,都顯得突兀、橫亘的現代性問題,使得並不厚重的《文學的變幻之旅》,成為當下幾乎所有中文論集中極為鮮明的一冊;也成為從今天這個文學時代的上空,清晰劃過的一道“越界”的光,為今天的讀者、作家和論家,留下了超越中文的更為寬廣、獨特、自由的論說和飛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