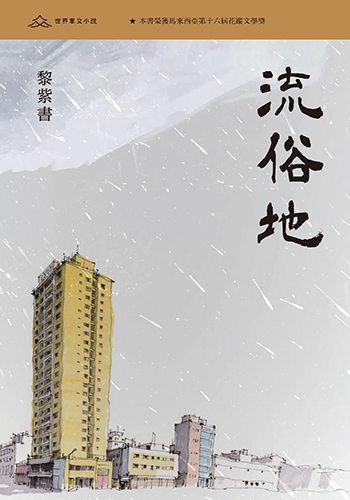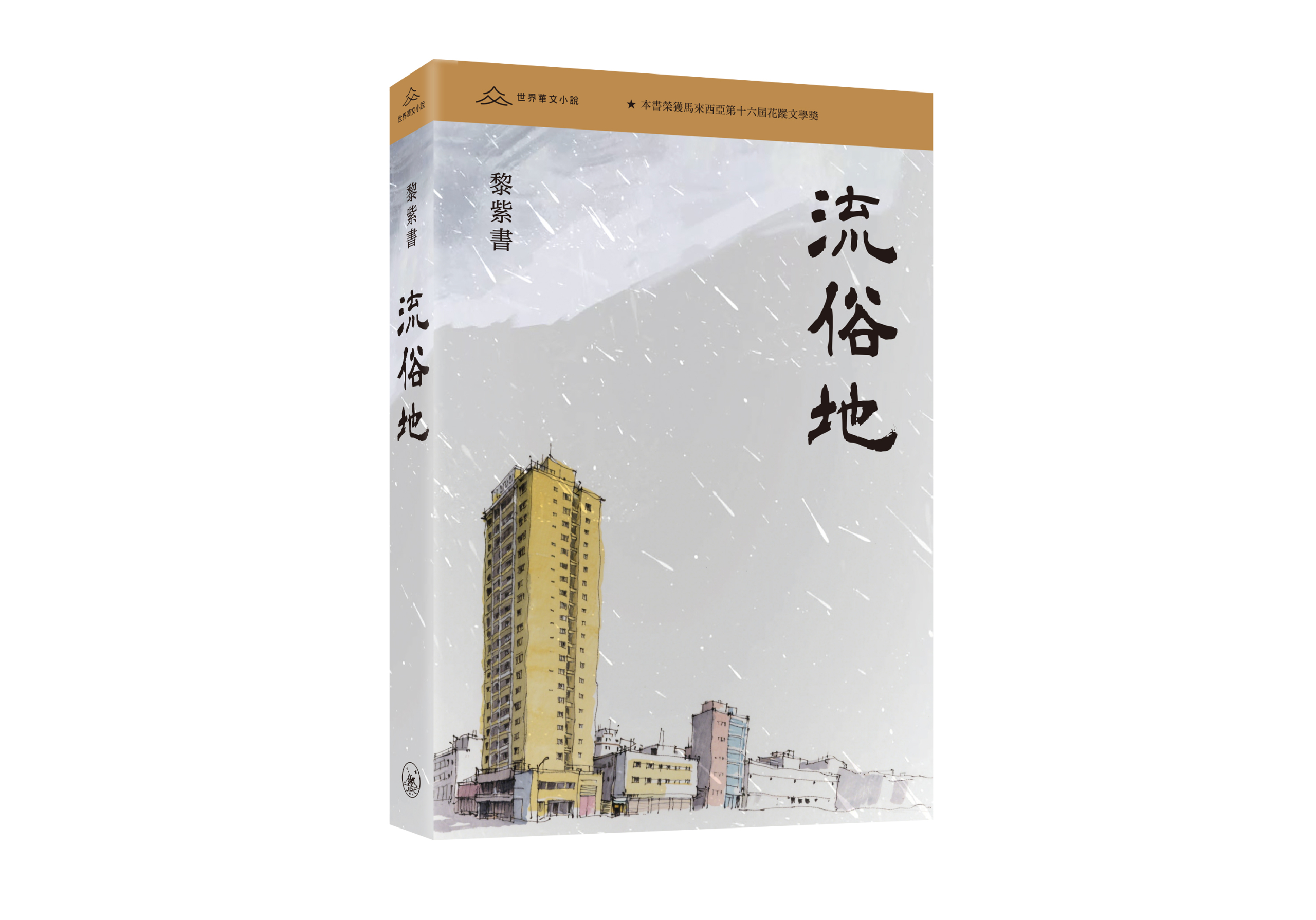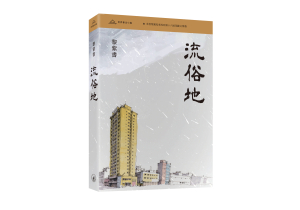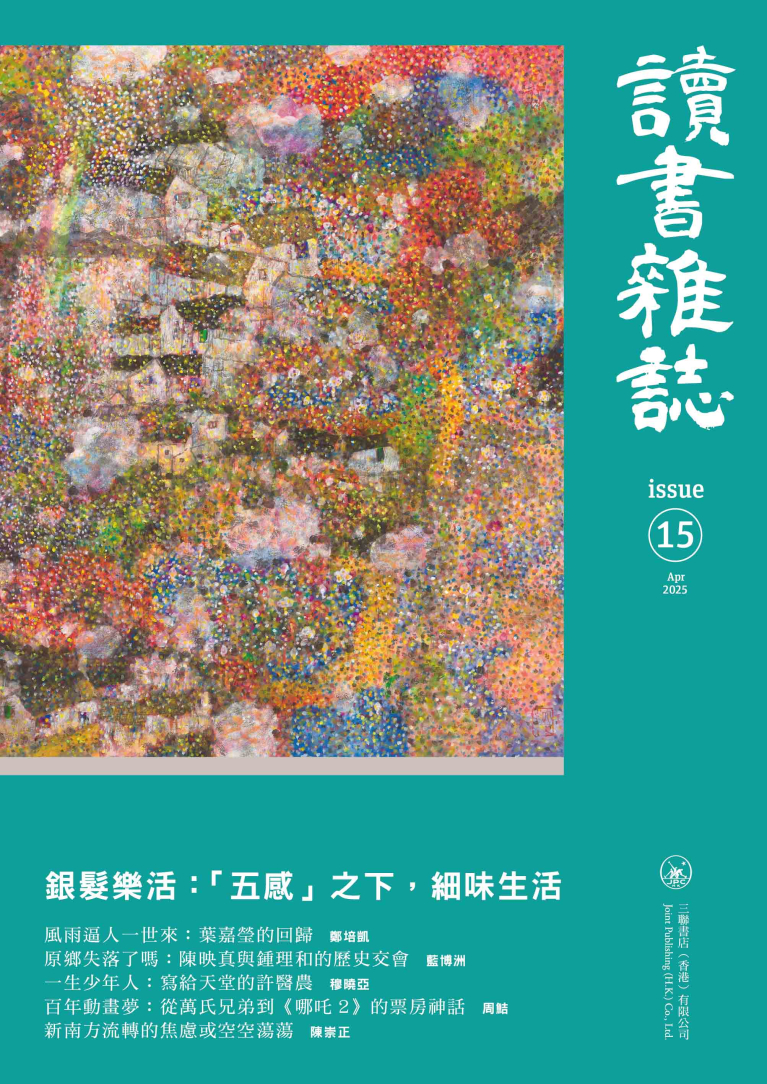流俗地(普通本)
簡介
馬來西亞,錫都,終年多雨。近打河畔「樓上樓」組屋居住著各色俗人,發生著各樣俗事。這些卑微與瑣碎,一同浸潤在熱帶雨林燠熱潮濕的空氣中。
少女銀霞天生目盲卻心清如鏡,成日居家編羅織網,亦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在與生俱來的困頓裏奮力劈開一片天地。當一切看似充滿希望的時候,不幸卻悄然降臨。
俊逸浪蕩的大輝、天資聰穎的印度律師拉祖、八面玲瓏的馬票嫂、從寄人籬下到脫胎換骨的蓮珠⋯⋯人們在各自的命運洪流中掙扎,卻始終葆有韌性,平凡生命的強悍與詩意在在皆是。
黎紫書以「流俗」為鏡,映照出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微光;以女性獨特的視角和經驗,細密縫綴歷史的經緯度,拓展了馬華文學的敘事圖景。「吾若不寫,無人能寫。」鉛華洗盡,她以最平實卻最自信的筆觸,為故鄉存史,鋪展出這幅色彩斑斕的文學浮世繪。
目錄
代序 / 001
歸來(之一) / 015
奀仔之死 / 020
群英 / 026
巴布理髮室 / 033
蕙蘭 / 041
嬋娟 / 050
貓 / 056
蓮珠 / 065
迦尼薩 / 073
大伯公 / 082
美麗園 / 089
鬼 / 096
所有的路 / 107
密山新村 / 118
南乳包 / 125
百日宴 / 134
新造的人 / 144
十二歲以前 / 152
仨 / 164
良人 / 175
那個人 / 185
春分 / 195
夏至 / 205
公仔紙 / 215
遠水與近火 / 224
立秋 / 234
女孩如此 / 244
懺悔者 / 254
紅白事 / 267
奔喪 / 277
點字機 / 289
信 / 298
顧老師 / 306
二手貨 / 317
失蹤 / 327
惡年 / 335
囚 / 345
馬票嫂 / 360
一路上 / 369
歸來(之二) / 380
後記 / 397
作者簡介
黎紫書
1971年生於馬來西亞。自1995年以來,作品多次獲得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台灣《聯合報》文學獎及時報文學獎等。個人曾獲馬華文學獎、南洋華文文學獎、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獎」、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以及郁達夫小說獎等。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獲第四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已出版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微型小說集以及散文集等著作十餘部。
代序
一種新的馬華文學圖景的生成
徐則臣
在《流俗地》之前,我們對馬華文學有大致統一的想像:書寫殖民地文化,側重種族歧視與抗爭主題,開掘政治歷史和身份認同,展開熱帶雨林不同時代的瑰異傳奇,等等。這些書寫屢有強烈的宏大敘事衝動,即便僅作傳奇性的民俗展示,這展示也多半要附麗於宏大的場景。已完成經典化的作品如此,新生的作品也同樣如此。最近四年間,我做過兩屆馬來西亞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之一「花蹤文學獎」的小說獎評委。該獎參選者甚眾,每屆都少長咸集,新人與老手並舉,走到最後的,創作上最為成熟、藝術上最為自洽者,也不外乎這幾類。這些小說與已被尊為經典的作品,如李永平的《婆羅洲之子》《吉陵春秋》《大河盡頭》《雨雪霏霏》,張貴興的《賽蓮之歌》《群象》《猴杯》《野豬渡河》,黃錦樹的《夢與豬的黎明》《大象死去的河邊》《雨》《烏暗暝》等十分相似。就閱讀體驗而言,口味偏重,故事、敘述、修辭普遍華麗、黏稠、浩蕩、糾結,燠熱與潮濕中隱隱躁動著暴力與生殖的氣息。而這些洶湧壯麗的異國故事,無疑也已成功地讓我們建立起對馬華文學的共識。
在當下的馬華文學界,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三位無疑是典範,以三者為代表建構出的馬華文學想像,也足夠地深入人心,以至於作為他們後輩出道的黎紫書,一定程度上被他們巨大的同質化陰影所遮蔽。即便時日遷延,後者聲名漸起,她的馬華書寫可能也會因其非典型,更多是作為馬華文學的一個多元補充被論及。至少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裏,尚未將其列為馬華文學的典型代表。十四年前,我曾作為黎紫書的責編,將她的短篇小說《生活的全盤方式》刊發在《人民文學》二○一○年第四期上。該短篇也作為黎紫書「自己重讀過最多遍的小說」,被收入她本人「最滿意的」短篇小說集《野菩薩》一書。在這篇小說中,除了個別異於中國大陸的漢語表達,很難找到鮮明的「馬華性」,那些詞語可能來自東南亞的很多漢語族群。小說也保持了當時黎紫書的先鋒和現代,將顧城的詩歌穿插在一個唐突的、溢出了日常認知的兇殺案中,看上去相當「文藝」。或者說,小說是以顧城的詩句為線索,互文性地講述了一個懸疑但傳奇色彩稀薄的小鎮殺人事件。在故事中,一個「自律而安靜」、可以「默默地完成所有事情的全部程序」的、曾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過的姑娘,在面對一個有理講不清的賣彩票的小夥子時,掏出剃刀,一刀封喉,然後在現場冷靜地報案自首。與標題「生活的全盤方式」之費解相似,小說也很難抽象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心思想」。
黎紫書的其他作品也多如此。她的小說習慣遊走在現實與荒誕之間,她也更鍾情於寫作上的翻新與實驗,如果非要歸類,我會把她劃入現代派寫作的陣營,視之為中國大陸先鋒文學的餘緒。黎紫書生於一九七一年,世界範圍內這個年齡的華語作家,多少都會受到中國大陸先鋒文學的影響,黎紫書寫作呈現如此樣態,不難理解。在黎紫書的作品中,作為故事背景的地域,這一現實主義小說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淡得幾乎失去了可供展開社會歷史批評的可能。即便她刻意以生長地怡保,也即《流俗地》中的錫都為背景的那些小說,「馬華性」都不是醒目的存在,作為符號的錫都多半淹沒在她更感興趣的人性與先鋒派的現代書寫中。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堪稱這種寫作的代表,視之為一個故事和結構的魔方亦不為過。小說講述了三個時空中的一個名叫「杜麗安」的女人的故事。故事套故事,一個故事推動和逼近另外一個故事。由此,「杜麗安」的人生形成了三進式庭院結構,一進之後又來一進,再來一進,小說繁複到了超載的程度。若非對「現代派」懷抱狂熱激情和巨大野心者,斷寫不出如此小說,這念頭都不會起。在黎紫書的短篇小說中,她也極盡「實驗」之能事。在短篇小說集《野菩薩》的中國大陸版序中,黎紫書寫道:「我喜歡在短篇小說的篇幅裏做各種實驗,畢竟它再先鋒、再晦澀、再難讀,也不過只有幾千至一萬來字,也就是這些實驗若不成功,並不至於給讀者帶來太大的『痛苦』;對於作者而言,即便失敗了的實驗作品,其書寫過程依然充滿創造者才能享有的苦痛與快樂。」
所以,作為「絕對是近幾年來馬來西亞文壇中長得最漂亮的鳳凰木之一」的黎紫書,其寫作走的是迥然區別於李永平等父兄輩作家的另外一條道路。她所呈現出的「馬華性」也無力與李永平等人分庭抗禮,當然也更難撼動李、張、黃等人經營出的穩固的馬華想像。到了《流俗地》,黎紫書又煥然一新,既繼續迥異於李永平等,又有別於過去的自己。也許若干年後,我們可以說,憑藉《流俗地》,黎紫書已然提供了一種新鮮且強大的馬華文學圖景。
《流俗地》版面字數28萬,在「長河小說」頗有回暖跡象的當下,算不得多大的「分量」,故事也不複雜,視為散文化寫作似也不太離譜。你想在小說中拎出一條邏輯井然、情節跌宕的整體性故事鏈,不是很容易。錫都近打河畔的「樓上樓」,相當於一處貧民區,住在這裏的人都想搬走,但生活窘困又無力逃離,反倒親密抱團起來。「樓上樓」住著三個小夥伴:華人盲女古銀霞、華人男孩何細輝、印度男孩拉祖,三小無猜,青梅竹馬,他們緩慢地在這個窄小的空間裏成長。炎熱潮濕、漫長瑣碎的童年終於結束,長成到青春期的他們紛紛搬離「樓上樓」,各奔前程,迎來同樣炎熱潮濕、漫長又瑣碎的成人生活。光陰荏苒,命運遭逢,大歷史總有變故,小生活也是一地雞毛。即便生死攸關,因為卑微和平凡,於各自狹隘的生活情境裏也弄不出多大的響動,但見生活沉默著運行,彷彿被世界拋離了軌道。不過大世界的消息,又屢屢如鹽入水一般滲透進他們的生活。他們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嚮往與喜怒哀樂,皆如螻蟻般遊走在這大小世界之間,可以眼見著他們生,也當可眼見著他們死。
成年的古銀霞做了電話接線員,每天接收四面八方的消息。上天遮住她的雙眼,但給了她一雙向世界敞開的耳朵和超強的記憶力。因此,她被世界拋棄的同時,陰差陽錯地又身居世界的中心。《流俗地》正是以她的視角展開,以三個髮小的成長為主線,經天緯地,鋪陳出與他們相關的群像式的地域與集體生活。
二
這裏是錫都,以錫礦馳名,採礦墾殖吸引了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咸來奔赴,形成多元共處的生活場景。三個髮小瑣碎凌亂的生活在盲女銀霞的視域中展開,在當下和回憶中移步換景、自由穿梭,部分章節和片段的連綴不乏意識流式的隨意和自在。很現實,忠直於生活和細節,但少有現實主義習見的宏大抱負,情節推進也非層層剝繭,而是風行水上,隨處成文。若論佈局,也只能是「無所用心」的佈局。這跟黎紫書過去殫精竭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結構與修辭不啻有天壤之別,與傳統的史詩更是格格不入,與典型的宏大敘事式的馬華長篇自然也相去甚遠。史詩與宏大敘事多要依賴一個壯觀的故事框架,要在一個獨特和闊大的歷史與現實語境中展開邏輯推演和命運演變。長於經營此類長篇小說的黎紫書的父兄輩作家,不會如此「散點」和「失焦」地去寫作一部《流俗地》。他們的興趣在於把螺絲越擰越緊,讓情節環環相扣,讓故事邏輯日漸壯大,讓人物命運越發緊迫,讓小說的故事、結構、人物,勠力同心、精誠協作。如此這般,他們筆下的國族大義、身份認同、反殖抗爭、雨林傳奇才能獲得更充分的張揚。
黎紫書想要的不是這樣凝心聚氣的宏大敘事。董啟章在為《流俗地》馬來西亞版所作的序中說:「《流俗地》沒有《告別的年代》那種立傳寫史的偉大意圖,好像完全是為了說好一個故事和說一個好故事,所以在主題和形式兩方面也貫徹了『流俗』的宗旨。」而黎紫書在該書「後記」中也以夫子自道相呼應:「我沒有費心去搜索好故事,也不去搜挖或創造非凡的人物,而是決心要往另一個方向走——把一群平凡不過的人放在一起,說他們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這樣的故事本質上必然樸實無華,不會有多少意料之外的轉折與驚喜。它肯定缺乏戲劇性,也不具備『好故事』的特質與要素……」董啟章的「好故事」與黎紫書的「好故事」顯然不是同一個意義上的「好故事」。黎紫書所謂的「好故事」,是那些「意境氣勢都澎湃磅礴」,如《吉陵春秋》《大河盡頭》《群象》《猴杯》《野豬渡河》的故事。這些「澎湃磅礴」的小說才需要非凡超越的人物,需要絢麗與豐贍,需要斗折蛇行和跌宕起伏的戲劇性衝突,以便把一個個壯闊的悲劇或正劇山呼海嘯地推向高潮。黎紫書不需要這些,她只想講一講流俗之地平易漫漶的生活與風俗,「寫一部有很多人,有許多聲音,如同眾聲大合唱般的小說」,「以一幅充滿市井氣俚俗味的長卷描繪馬華社會這幾十年的風雨悲歡和人事流變」。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黎紫書為什麼拒絕《告別的年代》《野菩薩》中她已操練順手的方式,轉而冒險作「流俗式」的書寫?
每一個小說家都無比清楚,自己對一個整全的、超越性的好故事有多依賴。對絕大多數作者、讀者和評論者來說,判斷一部小說的完成度,都是取決於小說中故事的完成度;判斷一部小說成功與否時,也主要取決於小說中故事的優劣。黎紫書寫作二十多年,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她執意逆行,底氣所從何來?她可能會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流俗地》中的生活與故事應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接近作者自身的經驗,如此落筆,首先當是自我表達的需要。也就是說,在黎紫書自認為「身體不行」,「此生沒有能力寫上幾部長篇」,「搞不好這就是『最後一部長篇』」的背景下,決意要「用破釜沉舟般的心,將心目中想像的小說——《流俗地》裏的一長卷浮世繪,我所知的家鄉,一筆一筆勾勒描繪出來」。這事要做。在〈從觀念拯救時光——關於《流俗地》的對話〉中,她說:「馬華文學創作者人數稀少,你不把屬於自己的這一份體會和經驗寫出來,幾乎可以肯定,它就會被淹沒在一浪一浪的『歷史』裏,不會浮上來了。」這事不僅要做,這事也應該做。《流俗地》是有備而來。黎紫書在選擇該小說的內容和形式時,有著清醒的自覺,她要為家鄉怡保存史,所謂以小說的形式為時代留一部信史,同時也為自身的經驗立傳。
但內容和形式的選擇從來都不局限於藝術本身。為什麼寫這個而不寫那個,為什麼要這麼處理而不是那樣處理,在黎紫書那裏,這些肯定也是問題。美國學者傑姆遜認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因此應該把這些小說當作民族寓言去閱讀。必須承認,傑姆遜的觀點有其客觀性,差不多也是關於文學的共識。大約也因此,我們對馬華文學的期許亦不能外。黎紫書對此有自己的看法:「我們的『小說種類』太少了,因為所有得到(權威)認同的作品,都得馱著『歷史』這個重負,寫雨林、馬共、國族寓言、華人創傷和身份認同。它們確實讓馬華文學讀起來特別宏大(和嚴肅),但你能想像一個國家裏的某個民族,世世代代就只面對這麼一個問題,除它以外其他什麼都不重要,也不值一提,所以就只能接受這麼一類文學作品嗎?所謂馬華文學的代表作品,除了這一種以外,你想不想得到其他的?」可見,黎紫書規避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來講述「流俗地」的故事,正是基於對程式化的馬華文學想像的突圍,也以此來展示另一個維度的馬來西亞歷史與日常。這從她對「流俗地」這一小說標題的選擇可見一斑。黎紫書說,小說寫完後,發給一些編輯朋友看,並非大家都喜歡「流俗」二字,但她堅持。一者,「流俗地」三個字湊起來很有意思,流的是水,地意味著土,俗是人攜著谷。在水與土之間,在動和靜之間,民以食為天,小說想寫的也正是這些。二者,「流俗」也指小說中都是無力超脫的人和事,眾人皆俗務纏身,升不了天,終要落入泥淖做個俗人。這個書名之返璞歸真、親近自然和彰顯人性一目了然。這一回她要「接地氣」,正視煙火人世了,所以一改《告別的年代》的高蹈式寫作,降下身段,讓絢爛歸於平淡,一頭扎進風塵僕僕的歷史和日常裏。
這種歷史與日常是卑微、瑣碎的,家長里短的,個人化的,宏大的、象徵的、隱喻的、寓言的種種意象和套路不在古銀霞們的生活之內。但他們庸常的似水流年中,是否就沒有歷史?也不是。也就是說,黎紫書儘管讓自己的筆低至日常的塵埃裏,但並非沉溺其中不去抬頭看天。歷史的風暴自天而降,必然要波及芸芸眾生。問題在於波及誰,如何「可信地」波及。小說中涉及的時間跨度大約五十年,這半個世紀中自然發生了很多足以改變錫都、改變馬來西亞,乃至改變整個世界的事件,比如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比如二○一八年的馬來西亞大選,比如網絡的興起。只不過這些歷史是潤物無聲地滲入日常生活的。黎紫書自述:「小說裏頭確實貫穿著一種不明顯的『歷史意識』,但它融入在小說裏,與流動的時光融為一體。」也就是說,即便黎紫書無意去觸碰宏大與歷史,但宏大與歷史自然地就包含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沒有人可以脫離時間而存在,「光是把這五十年的社會面貌寫出來,竟然都成了歷史」,「如今時代飛速發展,一代人的經驗與記憶,花不了一代的時間就成了歷史」。
三
既然所有的事件都必然沉澱為歷史,所有運行在時間中的日常生活,不管大人物、小人物的,大事件、小事件的,最終都必將成為歷史這一巨大建築的構架與素材,那麼大可不必為日常生活書寫的「歷史性」焦慮。當然,對黎紫書而言,這絕非「躺平」的策略,或許更在於她洞悉了歷史與文學間的關係。毫無疑問,所有的歷史都重要,大歷史更重要,但具體到文學,卻並非所有歷史都重要,也並非所有歷史都可以通過文學的方式有效地呈現出來。它必須成為「文學化的歷史」才能夠有機地融入作品,否則就是外掛的裝飾,就是為歷史而歷史,就是拖根掃帚裝大尾巴狼。
如何才能有效地「文學化」?歷史只有與人物休戚與共,發生血肉聯繫,進而內化為人物命運的基本推動力,才算真正實現了「文學化」。歷史無口無身,無力走到時間的前台,要附著於人物身上方能言行;歷史的變換與影響,亦須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生發與傳播。《流俗地》深諳其道。比如小說述及「五一三」事件的後遺症,表現在「暴亂的喧囂已經化為苦悶的象徵」,「華人遭受二等公民待遇,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屈居劣勢,底層社會日積月累的生活壓力,無不一點一滴滲透、腐蝕小說人物的生活」;二○一八年五月九日的馬來西亞大選,在小說中也是通過選舉前後的生活場景和投票現場,以及人物等待投票結果和結果出來後的感受體現出來的。古銀霞在那一晚錫都華人圈的狂歡中有所共鳴與共情:
真有那麼一瞬,也不知那是什麼時辰了……有人喊出了一聲歡呼。那聲音亢奮而充滿激情,比美麗園中唱《苦酒滿杯》的聲音與那一套卡拉OK伴唱器材有更大的震撼力,甚至也比城中所有回教堂同時播放的喚拜詞更加澎湃,以至那一排房舍共用的一長條屋頂輕微晃動了一下,像某種巨大的史前爬蟲類忽然甦醒過來,聳動一下牠發僵的脊椎……銀霞聽到滿城歡呼……電視中的講述員用喊的也不行,他的旁白被背景裏洶湧的人聲和國歌的旋律淹沒了去。
大歷史在這一刻進入了古銀霞的生活,也進入了錫都人的生活。作為大歷史的馬來西亞大選,想必可能鮮活地留存在文學裏了,因為它已經融入小說中人物的日常生活裏。在那一晚,這世界上定然還發生了無數大事件,有些甚至已經或者將要改變整個人類的發展進程,但它們沒能及時地與古銀霞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聯繫,只能被《流俗地》排除在文學之外。倘若要尋那些大歷史、大事件,只能祈靈於別的記載或文學了。文學中的歷史,與文學元素相輔相成和諧共生方稱得上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至大的國族與歷史,也須彌散進日常與個體才算真正成立,如鹽糖可溶於水,如草木能扎根山。
當然,《流俗地》的章法佈局,黎紫書對日常生活之看重,與她藝術上的返璞歸真和敘述的自信也須臾不可分離。小說「後記」〈吾若不寫,無人能寫〉,照作家的說法,這一論斷源於經驗的差異,所以該種經驗和小說「我若不寫,以後也不會有別人能寫」言之成理。但焉知又不是出於藝術上的自信?寫作二十餘年,對小說的理解與見識、技藝上的磨煉,足以讓黎紫書胸有成竹。如其所言:「一直都在等待人生中適當的時機,等自己有了足夠的見識與積累,並且對自己的寫作能力有足夠的自信,可以向年輕時的夢想回身致意。」「適當的時機」意味著有了足夠的自信,黎紫書在接受《新週刊》的採訪時說,這個時候,她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會追求寫出別人所期待的那種好作品,也不再想要得到其他馬華作家或學者的認同」。既可以無視他人的評價,也可以跳脫既有的區域性寫作傳統和個人寫作慣性,她要「自自在在地」去寫自己喜歡、認可的小說,而她「骨子裏就是那麼一個自以為在開天闢地的人」。那麼,更待何時?
日常生活的書寫因其瑣碎和缺乏戲劇性,倘想避免平庸又吸引讀者,尤其需要真功夫。十八般武藝黎紫書如今樣樣具備,打開小說即可一目了然:下筆冷靜又深情,因為能夠深入人物內心,針尖麥芒的小事也能搖曳生姿;更兼王德威評價的「最大的成就是沉穩」,《流俗地》便成功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或當歸功於黎紫書的返璞歸真。這不僅指修辭上的洗盡鉛華,娓娓道來,平實而不炫技,更在於她對日常生活所抱持的那份尊重與平常心,在於她對煙火人間所懷有的平等視角,對眾生的無差別心和有節制的悲憫與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