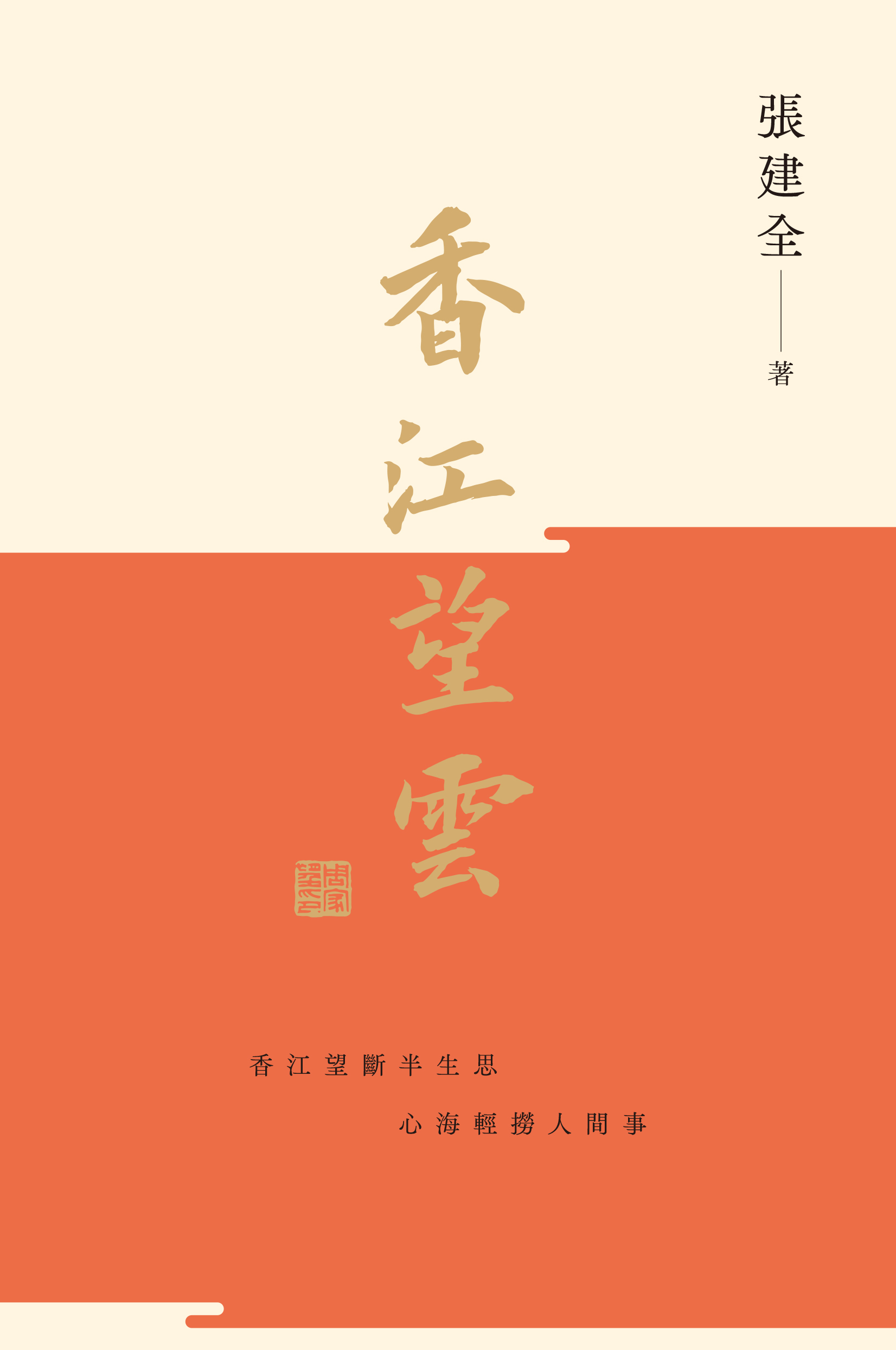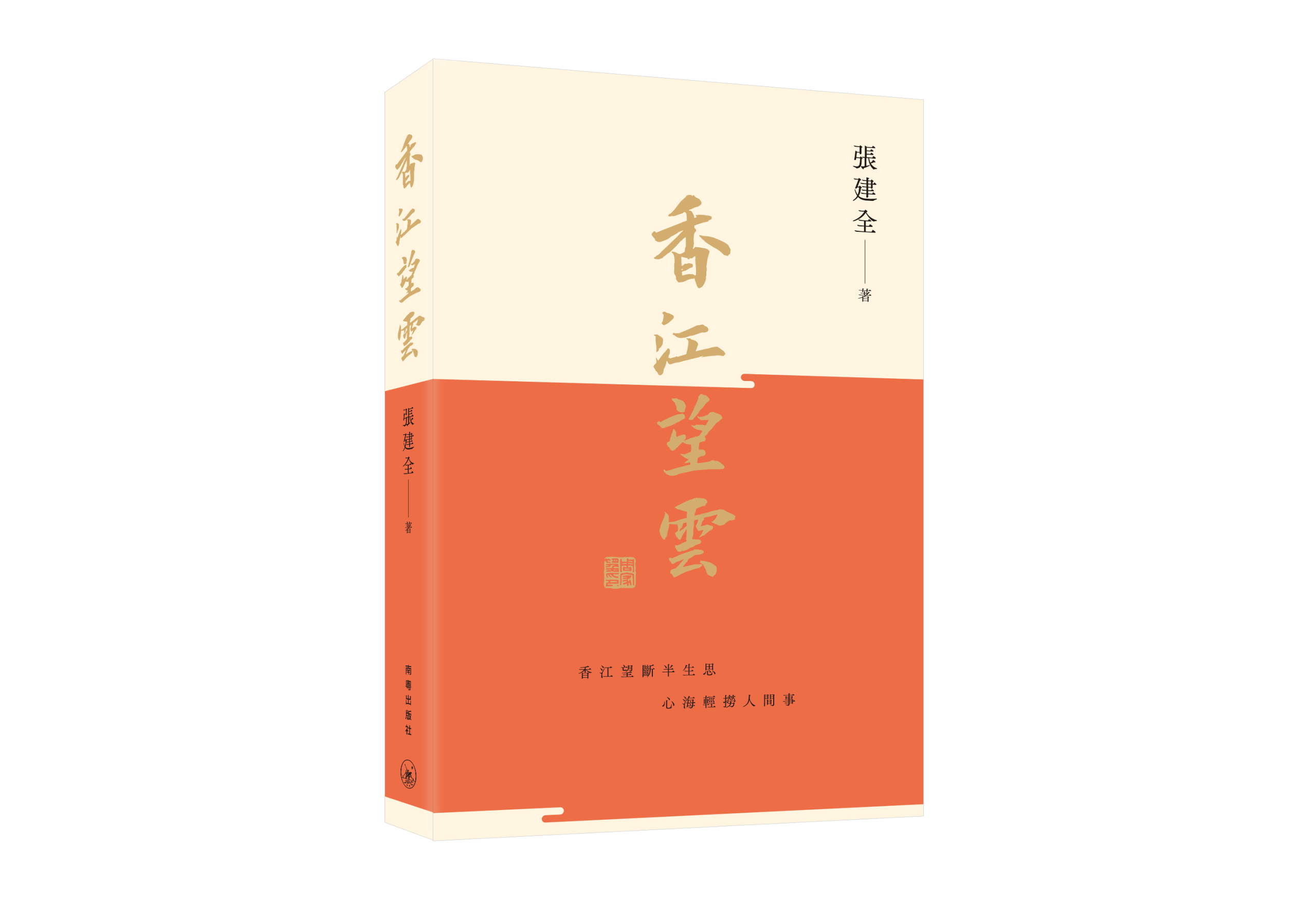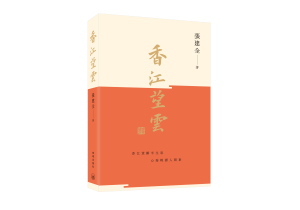香江望雲
簡介
從關中原野到香江雲天,以筆為舟,橫渡時代與地域之界限。《香江望雲》是一部富有個人色彩與時代厚度的散文集,記錄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從農村少年到軍旅幹部、企業管理者的生命旅程。書中四輯內容涵蓋嶺南風起、香江故事、域外所見與歷史沉思,視角橫跨城市與鄉村、中國與世界、現實與記憶。
《香江望雲》既是一部個人心靈史,也是中國幾十年社會變遷的民間見證。這些散文不僅記錄了作者在深圳、香港、北京等地的生活軌跡,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歷史現場。無論是香港高樓間的思索、沙頭角中英街的風雲往事,還是對唐宋歷史人物的凝視,都兼具知性與情感。
目錄
序 / 紅孩 i
自序 vii
輯一 嶺南風起
回望羊城 003
沙頭角中英街 011
初到香港 017
高樓不問人間事 024
重逢阿美娜 032
香港地名考 040
香港高樓說 046
俠之大者:金庸 055
好聽的粵語歌 064
我和車的故事 070
港澳碼頭 079
相守相望 088
輯二 香江望雲
多少魅影出東瀛 095
別了,彭定康們 107
閒聊一個彈劾案 115
USA總統開罵 123
ICAC法不容情 129
遙遠的豪門血案 136
何言兄弟似手足 148
甜甜的幻影 154
輯三 域外觀感
我住池袋本町 167
影壇有一尊雕像 171
伊豆半島的舞女 176
非凡的足跡 179
慕尼黑消失的啤酒館 186
溫斯萊特的革命 192
慘死街頭的茜茜公主 197
血腥的校舍監獄 204
硝煙遮蔽親友圈 210
偷襲珍珠港 215
錯誤的戰爭 219
我和曼特先生 224
輯四 史海拾貝
神都大變局 231
李顯皇帝之死 245
三讓帝位說李旦 254
李隆基何以弒三子 260
玄宗回馬楊妃死 269
踩著唐人的腳印 275
仰望蘇東坡 281
我看故宮幾十年 286
紫禁城中珍妃井 293
淒淒的婉容 303
津門慶王府 311
忠王李秀成 318
胡雪岩的桃花劫 327
薄塵難埋袁項城 335
瀟湘激盪英雄氣 347
江城幸有黃鶴樓 354
蔣氏父子的背影 362
驪山之上兵諫亭 367
白公館的哀思 376
長城內外是故鄉 385
古人寫就《愛蓮說》 388
少林尚武育男兒 392
尋覓桃花源 399
永遠的高營長 404
作者簡介
張建全,作家、詞作家。籍貫西安,常居北京、香港。北京作家協會、中國散文學會、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會員,北京市朝陽區作家協會副主席。連續三年榮獲中國散文年會大獎。其小說、詩歌、散文、歌詞散見於國家及省級文學期刊。曾出版小說集和散文集數種。
名人推薦
種過地、當過兵、經過商的張建全先生以他豐富的閱歷和睿智的心靈,開掘出目光所及之處的美好、良善和機趣,情之所至,撰寫了大量散文,尤其是對香港、澳門、深圳等地的描寫,別開生面,見識獨到,令讀者耳目一新。散文集《香江望雲》其字裏行間凝練且富有生氣,融入了他不斷跨界拓展的果敢,以及坦誠的人生感悟,是有心人借鑒和參悟的明師諍友。——中國散文學會會長 葉梅
香江的雲,承載這座城的記憶。翻開這本書,香港的市井百態躍然紙上。——甄子丹
序
散文的天空無比燦爛
紅 孩
國慶假期,很多人都到各地旅遊打卡,我則坐在家裏讀散文。很多朋友說,你幾十年如一日地寫散文、編散文、寫評論,如今又大張旗鼓地做有關散文的公眾號、視頻、直播,簡直著了散文的魔。我聽罷一笑,說,人這一生總得有一兩件愛好,最好能讓人著魔,不然,整日閒得無聊,一天天的日子可怎麼打發呢?
我喜歡散文,寫了幾十年,到了最近幾年,似乎才悟出了點門道。我不止一次說,寫散文如同參禪,不管你多麼勤奮,多麼有耐力,最終你得有瞬間永恒的覺悟,即所謂的一念。不然,你所有的努力都將無果而終。我這麼說,並不是給許多有志於散文寫作的朋友潑冷水,說泄氣的話,藝術的規律本就是如此。那麼,有人就會問,什麼樣的果才是散文的正念?我想說的是,一切果皆是果,怎樣寫好散文,什麼樣的散文是好散文,那就要看你的慧根了。我知道,所有的答案都並非答案本身。
生活即宇宙,宇宙是這世界最大的道場。文學也是個道場,散文是文學這個道場中的一個賽道,如果把散文也看做道場,倒也不妨。在散文這個道場裏,修行的人很多,古代得道者很多,諸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東坡等八大家。其實更寬泛點說,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先秦諸子百家,以及後來的司馬遷、諸葛亮、李密、王勃等人又何嘗不是文章大家呢!至於近現代,毛澤東、魯迅、胡適、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朱自清、冰心、老舍、孫犁、秦牧、楊朔、劉白羽、魏巍等,總該有上百人可以列舉吧。我之所以這麼縱向描述,無非是想說,我們的漢語言文學在散文這個道場裏,有著無數的先行者,他們以不同的經典作品,對散文這個文體做了最好的闡釋。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統一標準,對他們的作品作高低優劣之分。我只能說,在我們這個國度,散文的天空無比燦爛。
在八十年代,我上初中的時候,第一次知道了「散文」這個詞。從那時,我在心中把散文家當成神明一樣供奉,他們的名字依次是魯迅、冰心、朱自清、茅盾、碧野,我銘記的散文有《紀念劉和珍君》、《藤野先生》、《櫻花讚》、《背影》、《荷塘月色》、《白楊禮讚》、《天山景物記》等。當老師講到「散文貴在形散神不散」時,我是懵懂的,直接的理解就是寫散文不能跑題,要有中心思想。誰能想到,在幾十年之後,我不但寫散文,還編輯散文、研究散文,為散文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採風、評獎、研討、出書等事宜。尤其令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在二十年前,我見到了「散文貴在形散神不散」的首倡者肖雲儒先生。1963年,肖先生寫了這篇文章,當時他還只是個在校的大學生。如今我們成了忘年交,他還專門撰文對我提出的「散文的確定性與非確定性」表示了高度認可。另一件讓我感到驚訝的事情,是在與今年新結識的文友張建全先生的一次聚會上,他詳細給我講了他到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尋訪魯迅足跡的經歷,以及所考證的有關藤野先生的軼事,讓我對魯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不僅做到了知其然,而且還做到了知其所以然。
張建全六十年代初出生在陝西西安市高陵縣白蟒塬下十里村,十八歲參軍入伍,輾轉於湖南、北京、河南,六年後轉業落到西安。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激勵了無數年輕人的創業夢想,偶然的一次廣州之行,使張建全的命運轉折到改革開放的潮頭深圳。在那裏,他親眼目睹了國貿大廈是如何拔地而起,令整個中國「當驚世界殊」的。我沒有張建全的港深經歷,但他置身於香港、深圳的高樓大廈之間,忽然想到把香港與遠在幾千公里外的陝西老家那個叫做十里村的村莊進行比較,這大大超乎我的預料。張建全在其散文《香港高樓說》中寫道,在關中老家,蓋房對於一個農家是頭等大事,不僅關乎生存需要,更關乎個人和家族的面子。我想,這深圳國貿大廈的建設就關乎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它同時也代表一種面子,很大很大的面子,不過這個面子我們中國必須要有!多年以後,張建全舉家從深圳來到北京,他所選的住所就在北京國貿大廈附近,這是機緣巧合,還是內心的歸屬,張建全內心自然明白。
我結識張建全,不是因為他是個成功的企業家,或者是某明星演員的家屬,完全是由於他熱愛寫作,對文學有著執著與虔誠。張建全的文學夢,我認為在他的老家渭河北岸白蟒塬下就開始了。在陝西關中地區,有著很多大大小小的「塬」,如我們都知道的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塬,還有神禾塬、少陵塬。何為「塬」,就是由南部秦嶺山地向北部平原伸展過程中形成的遼闊渾厚的土台子。站在塬上,你會自然想到「原野」這個令人充滿想像的詞,你也可以向遙遠的對面山坡坡吼上幾聲秦腔。
張建全的文學之花開在深圳。當他的小說處女作《阿美娜》發表在深圳《特區文學》引起關注甚至引發爭議之時,他覺得他可以吃文學這碗飯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當他拿著稿費請當地文友吃飯時,才發現那稿費不夠一頓飯錢,這讓他感到尷尬、窘迫甚至是恥辱。也就在那一刻,他決定暫時放棄文學,去經商、去下海。我相信,在九十年代初,特別是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像張建全那樣棄文棄政棄國企,投身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從張建全後來的諸多小說、散文、紀實文學中,我雖然不能了解他的全部經歷,但卻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文學是能讓人著魔中毒的。張建全不論身處中國的深圳、香港、澳門、海南、湛江,抑或是到了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他始終保持對生活的敏感,不忘對生活的觀察、細節的發現,即便是當時沒有寫出作品,也會在筆記本上留下關鍵的詞語。我說過,文學就是我的經歷,一個寫作者的經歷就是他的寫作財富。比起普通的人,張建全無疑見多識廣,但他也時刻告誡自己:一個人的眼睛再大,也不會直接看到自己後腦勺處的頭髮;身處城市中心,也會忽視周邊的磚石瓦片、樹木花草。我注意到,張建全在生活中,確實有著基建工程兵的那種勇氣和耐力,這種性格也必然會成就他的事業。譬如他第一次當經理,談成的第一筆買賣就險些擱淺在湛江,賠本不說,臉都不知往哪放,那可是自己的第一次單飛啊!於是,他硬著頭皮去找只有一面之緣的老兵局長,居然把一盤死棋給下活了。再譬如,他為了方便在香港的生活,百折不撓地學開右舵汽車;到世界各地「自駕遊」,語言不通,他完全通過手機去實現自己的一切。看到這些經歷,我不由發出感嘆:他活成了高倉健!
我和張建全都屬六十年代人,他比我長幾歲。我們都從農村走出來,進入城市。讀張建全的散文作品,我常為他涉獵的廣泛感到驚奇,如音樂、電影、歷史、文學、人文、經濟,讓人看後不免產生多重的獲得感,正如我所提出的判斷一篇好散文的標準:「獲得多少知識(信息)的含量,情感的含量,文化思考的含量和藝術審美的含量」,顯然,張建全的散文大體都做到了,有許多地方還讓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寫故鄉的高陵塔,寫到那塔本是唐塔,其地位不可小覷,只因它生在西安的北郊外,就不像西安城裏的大雁塔、小雁塔那麼頗負盛名,就使我想到小時候家門前的無名小河,想到了我們許多的無名小人物,想到了修長城開鑿大運河的那些千百萬的勞動人民。還有,張建全多次去故宮,每次去都有不一樣的感受。在故宮角樓的咖啡館,在走出神武門的瞬間,他會覺得做今天的老百姓好,故宮是可以隨便出入的,不像古代的文官武將王公貴族,出入要等待皇帝的詔書。
這些年,關於散文我多有論述,張建全是個有心人,他把我的散文理論一一找來細讀,有了心得體會,他還要在書上劃線寫感想,甚至還把某些共鳴的理論書寫成幅,如「散文是說我的世界,小說是我說的世界」、「散文的寫作是從我到我們的過程」、「散文的確定性與非確定性」、「莊嚴國土 覺悟人生」等,既讓我感動,也讓我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知音。看了張建全的一些作品,逐漸對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認識。我想對他說,散文寫作沒有固定模式,任何的模式都可以嘗試,只要它適合自己的語言節奏,足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國慶前,他把散文集書稿《香江望雲》發給我,希望我能為其寫序,我則欣然受命,樂此不疲,原因是我歷來認為一個人的經歷越複雜,其情感思想也就越豐富,直覺告訴我,張建全的散文一定會有看頭。誠然,這本散文集的書名叫《香江望雲》,內容肯定與香港相關,但也不都如此。如果把香江看作祖國陸地的南端,那麼往北看,則是整個中國,香江以外呢,當然是整個世界。也許,讀者在看本書時,是按作者編輯的四輯來看的,但我卻把整本書看作一篇散文,我覺得散文寫作不必過於拘泥,只要風箏不斷線,內容是可以上下左右紛飛的。在寫這篇文章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於國慶黃金檔上演了曹禺先生的經典話劇《原野》,主演是張建全的女兒張可盈。在觀看演出時,我就想,張建全從小生活在渭河北岸的白蟒塬下,而今日,他的女兒又主演了《原野》,這冥冥之中是一種偶然,還是一種必然呢?或許,從周恩來年輕時在日本留學期間所作的詩篇《雨中嵐山》中可以找到答案:「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到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謹以此為序吧。
2024年10月8日
北京西壩河
自序
嶺南也,大灣區也!
嶺南,是中國南方五嶺以南地區的概稱,以五嶺為界,與內陸相隔。五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大體分佈在廣西東部至廣東東部和湖南、江西四省邊界處。歷史上大致包括廣東(含海南、香港、澳門)、廣西和湖南省東部、福建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區。
「嶺南」是一個歷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嶺南建制的劃分和稱謂也有很大變化。現在提及「嶺南」一詞,特指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亦即是當今華南區域範圍。這一區域,如今有一個響當當的新名:粵港澳大灣區。
今人讀這段文字,會產生一個簡單而直接的印象:「噢!嶺南,大灣區,那可是一個好地方呀!」 但要是上溯到宋朝、唐朝呢?我想那時的人可能會說:「噢!嶺南,那可是個不毛之地,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去處!」那時,中原王朝想在物質生活和氣候條件方面,給罪臣們吃一些苦頭,亦想讓他們與首都的官場離得遠一些,以免他們再生事端,於是,歷歷數朝,便把嶺南視為貶謫官員之地。
李德裕(787—850)與其父李吉甫均為晚唐名相,經歷唐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兩度為相,在位七年有餘,後因黨爭傾軋,被排擠出京,謫居海南。《登崖州城》一詩,便是李德裕在海南所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
顯然,李德裕哀嘆海南距離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太過遙遠了,以至於「鳥飛猶是半年程」。他心情鬱悶,亦有遠離朝廷中樞,徒有報國忠君之心的悲憤之情。王讜在《唐語林》中有言:「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哽。」
相比之下,宋代的蘇東坡在貶謫廣東惠州、海南儋州時,卻秉持了他一貫的樂觀主義人生態度。 謫居惠州時,他有詩《惠州一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再貶謫海南時,他又寫《椰子冠》一詩: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
規模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
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蘇東坡詩文名篇太多了,但我覺得他寫於兩個謫居地的「水果詩」,最貼合他當時的心態,最能夠反襯出他身處逆境依然樂觀的性格特點。
他吃了荔枝,便笑吟「不辭長作嶺南人」,他把蠻荒之地看作盛產佳果之風水寶地;他吃了椰子,便「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以此自嘲自己乃「違時」之人。但東坡先生實在是掌握了命運的反轉大師,他總能在「違時」的命運面前,修得「順勢」或者「造勢」之功,最後終於高登人生境界之峰頂,成為神一般的存在。
顯然,如果撇開別的不談,蘇東坡看待嶺南要好過李德裕。李德裕在海南抑鬱而終,蘇東坡卻在人生歸去之前,迎來光明的晚霞。
公元1100年,宋哲宗病逝,宋徽宗繼位。他大赦天下,蘇軾由此得以離瓊北返。他原本以為自己會步李德裕後塵而老死海南的,未料想他的人生竟還有最後一次轉折。於是在他乘船過海途中,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這首七律最末兩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顯而易見,亦如「不辭長作嶺南人」一樣,蘇軾對於「九死南荒」,既有「不恨」之曠達,又有「茲遊奇絕」之欣然。
當然,這些文字皆事關嶺南舊事。時間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此嶺南已非彼嶺南了。作為一個關中少年,我的命運竟然神使鬼差地發生了改變——有幸擁抱嶺南、成為嶺南人。
我出生在陝西關中,具體地說,是在西安市以北的高陵縣(現已撤縣設區)十里村。我十八歲時當兵,先湖南,後北京,再河南,復又北京。六年軍旅生活屆滿後,我以部隊幹部的身份,從北京轉業到航天部陝西管理局下屬企業機關任職。一年後,我以未婚之身,又從西安調入嶺南之熱點新城深圳工作,時年二十五歲。
在深圳,我趕上了中國頒發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證,且獲得了自己一生不變的身份證號「44030119⋯⋯」。 顯然,只有戶籍在廣東的人,才能獲得這個身份證號碼。這個戶籍,強化了我這個陝籍廣東人的身份認同。
那時的嶺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而深圳更像是一艘名為「經濟特區」的巨輪,正在揚帆遠航。嶺南大地處處春潮湧動。
我在嶺南開啟了人生最重要的篇章,十五年後,我帶著在嶺南大城深圳完成的人生成果—成家、立業,又遷居北京。2015年,由於女兒考入香港演藝學院,我以陪讀家長的身份長期租住在香港,而後又受香港特區「優才」政策惠顧,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證(非永居)。於是,我在進入退休之齡時,開啟了今京港、明港京的自由往返的候鳥式生活。
也許是因為一生搬家頻繁之故,我在華夏東西南北的故地多到難以排序的地步。我已不能簡單地回答自己是哪裏人的問題。如果非要回答,我願意說:「我是中國人,中國無處不是吾之故鄉矣!」
我自認自己得益於好時代,我在嶺南的日子比李德裕、蘇東坡要好上千百倍。但他們是天之驕子,他們謫居嶺南便有詩文傳世。我雖不才,但既在嶺南,無論是長居或者短旅,亦帶著一雙好奇的眼睛,在不甘於「享受嶺南而無讚歌」的心態驅駛下,寫了這麼一組文章。結集時一看,我才發現這些文字要麼是帶著香港元素或者是以香港為主題寫就的篇章,要麼是立足於香港看天下、談天下的習作。當擁有金字招牌的香港三聯書店決定為這些文字出書時,我除了高興、感激之外,趕緊搜腸刮肚地取了一個書名:《香江望雲》。對照書中所收文章的內容,好像還算貼切。
散文是寫「我」的,於是,本書便貫穿著我的人生經歷: 「種過地,當過兵,經過商」。 看看,僅僅九個字,就勾勒出我的大半個人生。但「九字」經歷中所遇到的人、面對的事、產生的喜樂與悲苦,感受的成功與失敗,遇到的忠誠與背叛,引發的醒悟與疑惑,卻是再多的文字也難以寫盡的。
本書文章對應的正是我的人生腳步與心路歷程。當然,閱讀之缺乏,思想之不足必定在我的文字中紛紛露頭。好在我抱著求教的心態,認為敢於露短,才能知短、補短,也才能進步。
本書分為四輯:
第一輯:風起嶺南。此「風」乃中國改革開放之春風。 有了這一陣激盪不息的春風,中國才開啟了「春天的故事」的歷史新篇章。
我十分喜歡台灣出品的電視連續劇《八月桂花香》的主題曲《塵緣》,歌詞中有一句:「漫漫長路,起伏不能由我⋯⋯」它揭示了個人命運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與真相。
當我走出關中農村時,印象中嶺南亦即廣東、香港和澳門,還是和《西遊記》中孫悟空的花果山一樣,既遙不可及,又充滿幻想。雖然說命運「起伏不能由我」,但命運卻待我不薄,它讓我有幸成為一名深圳的國企幹部,且讓我有機會到海南房地產開發公司當「一把手」。而我們公司又與香港、澳門有著廣泛的業務聯繫。我的生活也隨著工作轉移,不斷地擴大活動範圍和社交層次⋯⋯幾十年過去,我猛一回頭,竟然發現自己具有為期不短的深圳居住史:更沒有預料到的是,我有幸深度地體驗香港的社會生活。
「風起嶺南」這組文章,寫的就是我這樣的人生經歷和與之呼應的人生感悟。而我是我同時代人中的一分子,我相信我的生活記錄具有「社會標本」的作用,想必會引起我的同齡人的一些共鳴。
第二輯:香江望雲。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大約分屬物質和精神兩個範疇。我在體驗香港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同時,好像對於發生在香港的人文故事更感興趣。「香江望雲」是因為香港有太多風雲故事,它們給我的印象太過深刻,且在我自認為有了一定的人生感悟的今天,總有「回頭再看」的衝動,也有用筆書寫的願望。當然,這些大到國家政治,小到夫妻糾紛的故事,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在這裏說的,盡是個人淺見。
第三輯:域外觀感。在我的理解中,我們「60後」這一代人,是在新中國恢復「高考」制度之前完成中學教育的,我們的「思想解放」與全國人民一樣,發端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中國由此開啟的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令我們在思想覺悟與工作實踐上實現了「三級跳」式進步:從沿海經濟特區,到港澳台,到世界⋯⋯熟悉那一段歷史的人,知道從「閉關鎖國」到「全面開放」,對中國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意義。
於是,我們出國考察,我們放眼世界,我們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精神做自己的工作,交世界的朋友,也看東西方的文明和五湖四海的風景。在這個過程中,我留下了「域外觀感」的文字,權且算是我的旅遊報告吧。
第四輯:史海拾貝。我以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觀。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或多或少,或深或淺,都能發表些自己的看法,只是要使這些看法成文發表,對於作者來講,便如同開卷考試一樣。
「史海拾貝」就是我的一張張有關歷史的答卷,我本來缺少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支持,沒有把文章示人的信心。但好在這些都不是史學著作,我只是用文學的眼睛看歷史,用個人化的感覺談古論今,即便偏頗,即便淺陋,那也是我的一點學習心得,用以拋磚引玉倒也未嘗不可。
此書出版,首先要感謝香港三聯的總編輯于克凌先生和參與編校的朋友們!